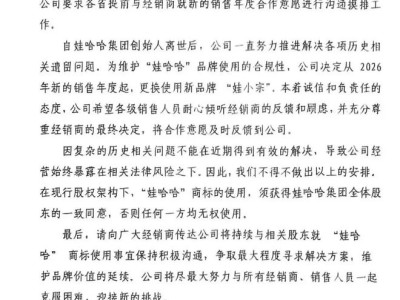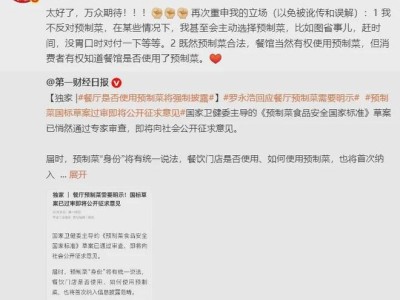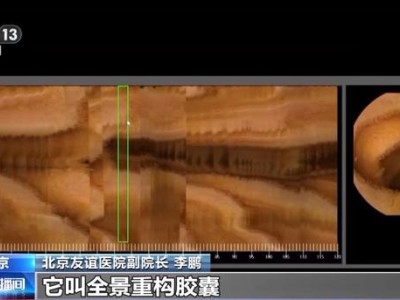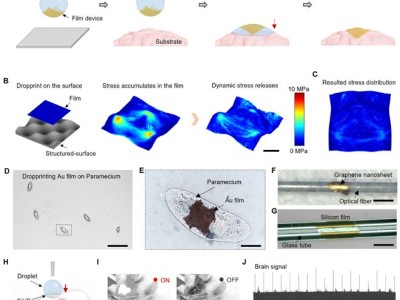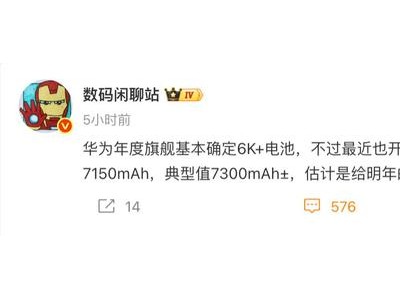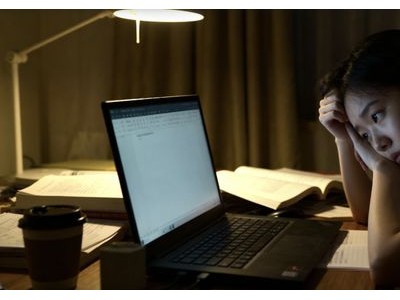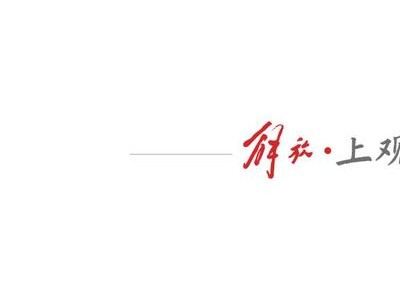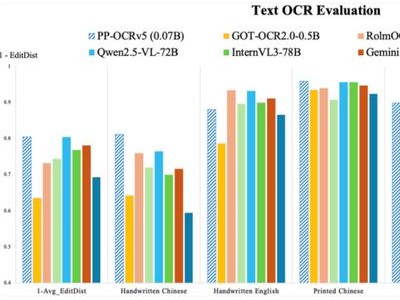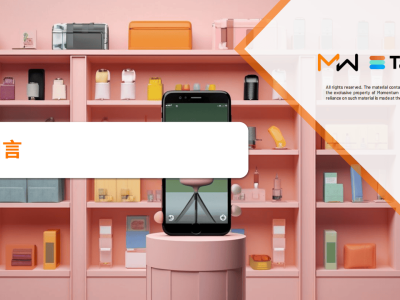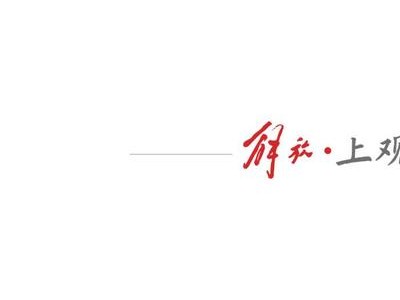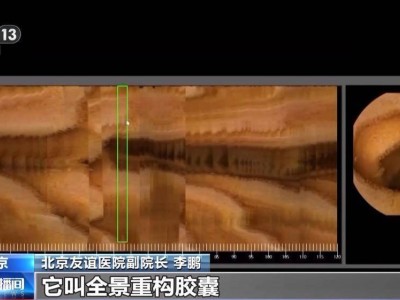民辦高等教育行業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寒冬。曾經被視為“教育印鈔機”的民辦高校,如今面臨招生困境與資金鏈斷裂的雙重壓力。廣東、云南、廣西等地民辦本科院校接連出現招生未滿額現象,部分院校甚至通過降低錄取標準維持生源,這一現象與十年前民辦教育行業的繁榮形成鮮明對比。

數據顯示,2024年民辦高校在校生規模突破1052萬人,較2016年的616.2萬人增長70%。這種擴張背后是資本的狂熱涌入——自2016年《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后,民辦高等教育被賦予“自負盈虧、自主定價”的合法身份,資本通過并購、擴建、上市等手段快速擴張。中教控股作為行業龍頭,旗下擁有14所院校、近28萬名學生,規模相當于清華大學的5.3倍、北京大學的6倍。2021年,該公司通過收購10所高校支出95.8億元,凈利潤達14.72億元,同比增長107.2%。
高利潤的秘密在于成本控制與專業設置。多數民辦院校側重文史、管理、商科等低成本專業,教學設備投入極低。財報顯示,中教控股2021年人均教學成本僅5400元,而人均收入達1.3萬元;希望教育同期人均成本4900元,人均收入1萬元。這種“低成本高收費”模式使行業毛利率普遍維持在50%以上,江西應用科技學院2018年毛利率甚至高達73%,超越同期茅臺的盈利水平。

但資本的狂歡在2025年戛然而止。多地民辦高校出現招生斷層:廣東14所民辦本科未完成招生計劃,云南連續6次征集志愿,廣西本科補錄取消最低分限制。更嚴峻的是,學生用腳投票現象加劇——廣東白云學院去年1477名新生放棄入學,上海某民辦高校首輪投檔“零報考”。大連一所民辦院校因債務危機停發工資,賬戶被法院凍結,卻仍要求學生十天內繳清學費,其法人代表背負35億元債務、35條被執行信息。
行業衰落的直接原因是生源萎縮與學歷貶值。隨著高考人數增長放緩,家長對教育投資的回報預期發生轉變。民辦本科每年數萬元的學費,加上教材費、住宿費等附加支出,四年總花費普遍超過15萬元,但畢業生就業競爭力并未顯著提升。在就業市場內卷加劇的背景下,家長開始質疑:“高價民辦是否等于高質量教育?”這種質疑直接導致招生困難,部分院校為維持運轉被迫大幅漲學費——2025年多所民辦高校學費漲幅達15%-30%,東莞城市學院年學費升至3.4萬元,上海視覺藝術學院更達6.8萬元,進一步加劇了家長的抵觸情緒。
從行業擴張到資金鏈斷裂,民辦高等教育的興衰軌跡折射出教育市場化改革的深層矛盾。當資本將教育簡化為“收入-成本”的商業模型,忽視教學質量與就業導向時,市場的反噬便成為必然。如今,這場持續十年的教育資本盛宴,正隨著生源減少與家長覺醒走向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