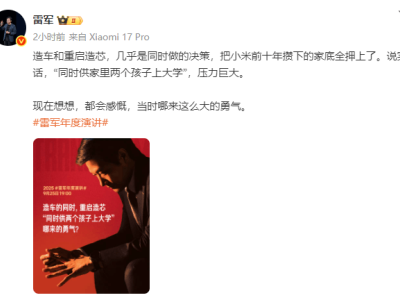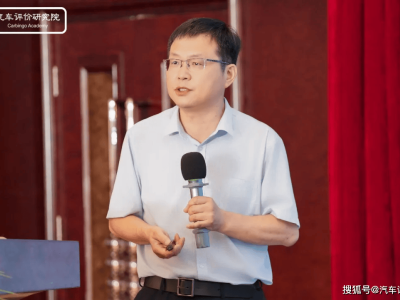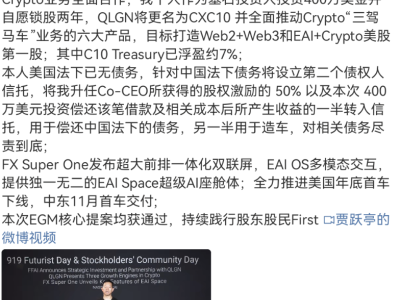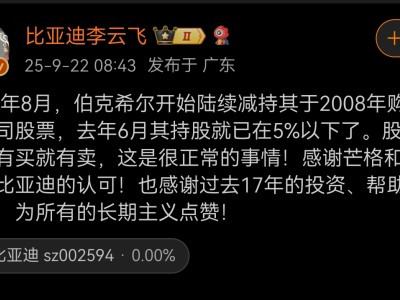當你在B站、小紅書或抖音瀏覽時,或許會注意到一個新現象:一些知名人物正端坐在錄播室,對著麥克風展開深度對話。這類內容被冠以“視頻播客”的標簽,正在中文互聯網平臺掀起熱潮。從陳魯豫與竇文濤的智識交鋒,到羅永浩與李想的行業對談,這些動輒數小時的長視頻節目,正以百萬級播放量引發關注。
視頻播客并非橫空出世的新概念。在YouTube生態中,這種音頻與視頻結合的內容形態早已普及。無論是個人創作者還是專業對談節目,通常都會同步制作視頻版本供用戶選擇。但今年以來,隨著B站、小紅書、抖音等平臺的集中發力,這一形式在中文互聯網市場突然成為焦點。羅永浩、陳魯豫等名人發布的視頻播客,憑借長時間深度對話和高質量內容,被視為播客行業商業化的新可能。
追溯播客的發展軌跡,其誕生與蘋果公司2001年推出的iPod密不可分。這款革命性產品讓音頻內容擺脫了傳統廣播的束縛,開啟了移動收聽時代。2007年iPhone的問世,則進一步將收聽場景從網頁轉移到移動端。盡管在北美市場,2012年蘋果獨立播客App的推出推動了行業爆發,但中文播客市場直到2020年聚合平臺“小宇宙”上線,才真正進入大眾視野。
經過五年發展,中文播客聽眾規模已達1.5億,占全國人口十分之一以上。這個群體呈現出獨特的“三高”特征:高學歷、高黏性、高潛力。數據顯示,49%的聽眾來自一線城市,29.8%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人均每周收聽時長達4.1小時。然而,這個看似優質的受眾群體,卻始終未能解決播客行業的核心難題——商業化。
獨立播客主林安自2019年開設節目《逆行人生》以來,深刻體會到行業困境。她觀察到,多數播客主最初都是出于興趣創作,第一期節目往往制作簡陋,動機純粹。“鏈接更多人”和“擴大個人影響力”是創作者的主要驅動力,而非商業變現。這種創作生態導致播客的商業化模式長期局限于廣告、付費單集和知識社群三種形式,且多數創作者只能依賴偶爾的廣告合作。
與美國市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8年美國播客廣告市場規模已達4.79億美元。這種差異部分源于中美兩國的出行習慣差異。在公共交通不發達的北美,汽車通勤帶來的“碎片時間填充”需求,催生了龐大的播客市場。而在中國,除一線城市外,長距離通勤場景較少,導致播客受眾高度集中于特定群體。這種細分市場特性,使得品牌方對播客廣告的投放始終持謹慎態度。
廣告公司媒介Liz指出,播客廣告投放存在雙向篩選。一方面,播客主為維護節目調性,常拒絕不符合聽眾畫像的廣告,如外賣優惠券等;另一方面,多數本土品牌將播客視為“預算充裕時的備選方案”,而非核心營銷渠道。這種局面導致,除奢侈品、個護等需要品牌形象建設的品類外,其他行業很少將播客納入媒體計劃。
視頻播客的興起,為行業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從成熟市場經驗看,視頻形態能更直觀地展示品牌信息,提升轉化效率,同時通過切片傳播延長內容生命周期。但這種升級也伴隨著制作成本的指數級增長。頭部制作公司JustPod的流程顯示,視頻播客需要專人負責嘉賓溝通、場景布置、現場把控等多環節工作,遠非傳統音頻播客可比。
這種成本壓力引發了行業爭議。部分聽眾認為,視頻播客偏離了播客“伴隨性收聽”的本質——如果需要專注觀看,那與普通視頻節目何異?同時,許多獨立播客主存在出鏡顧慮,社恐性格或外貌焦慮成為視頻化的阻礙。更關鍵的是,視頻播客究竟是播客的升級形態,還是一種全新的視頻內容類型?這個定義問題至今沒有共識。
在美國市場,播客的商業化路徑提供了另一種啟示。隨著播客融入日常生活,企業家開始通過這一渠道直接與公眾對話。挪威主權財富基金CEO等商業領袖的加入,使播客成為企業價值觀傳播的新陣地。這種模式下,廣告變現并非首要目標,品牌建設與公眾溝通成為核心訴求。這種“不掙錢掙名聲”的路徑,或許為中文市場提供了參考。
當前,B站等平臺提供的流量激勵,正在推動視頻播客的短期繁榮。但從業者普遍認為,長期來看,真正能脫穎而出的將是具有社會身份的創作者。如楊迪與金靖的對談節目所示,名人效應與專業內容結合的模式,更符合當前市場環境。視頻播客或許無法徹底解決商業化難題,但它正在改變內容分發的邏輯——讓優質內容更精準地觸達受眾,這或許是互聯網用戶最需要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