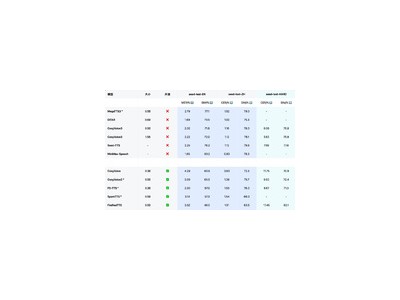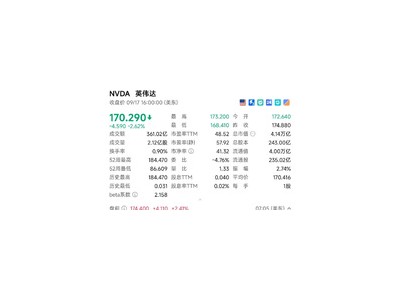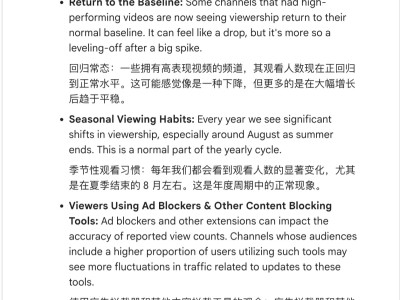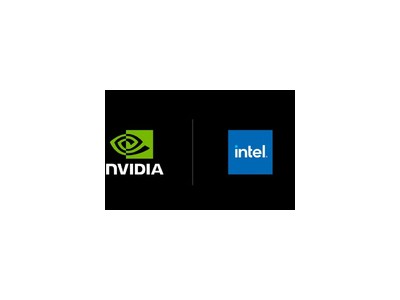村口那條蜿蜒的河岸,總讓楊雨漩想起兒時的夏夜。垂柳的枝條垂入水面,月光透過葉隙碎成銀斑,在河面與青石板上跳躍。那時她總愛在淺灘摸魚,直到聽見外公沙啞的呼喚:"漩兒,月亮跟著你走呢。"她便笑著跑開,抬頭望見那輪銀盤始終懸在頭頂,仿佛在無聲訴說著某種永恒的守望。
2006年秋夜,外公從工地帶回的舊包袱里裝著全村人的工錢。煤油燈下,他戴著老花鏡核對工時,將一萬元獎金分攤到每戶賬目中。那晚的月光格外清亮,楊雨漩看著外公佝僂著背,踩著泥濘小路挨家送錢。銀輝灑在他洗得發(fā)白的工裝上,連補丁的針腳都泛著柔光。有村民接過錢時紅了眼眶:"老楊頭,這錢你該自己留著。"外公只是笑著搖頭,煙斗里的火星在夜色中明滅,像極了天上墜落的星子。
十五年后,當楊雨漩站在鋼筋水泥的工地中央,咸澀的風卷著沙粒撲面而來。她忽然讀懂外公當年的沉默——那些被煤油燈熏黃的賬本,那些磨破的工程圖紙,還有月光下始終挺直的脊梁,都在無聲訴說著比訓誡更深刻的傳承。如今面對賬目上的模糊數(shù)字,她總會下意識抬頭望月,仿佛看見外公的煙斗仍在夜色中閃爍。
電話里,外公的聲音依然帶著沙啞:"干活要實在,做人要敞亮。"這些質樸的話語,像春日暖陽驅散工地的疲憊。她漸漸明白,家風不是刻在族譜上的文字,而是藏在煤油燈搖晃的光暈里,是布包勒出的手痕,是泥濘中始終干凈的鞋底。那些未曾明說的教誨,早已化作月光滲進血脈,在每個猶豫的時刻照亮前路。
如今楊雨漩的辦公桌上,總擺著從老家?guī)淼那啻杀1壮恋淼牟粌H是河泥,更是祖輩用半生寫就的答案:廉潔原是守住內心的澄明,像清水映月般坦蕩。當她在深夜核對賬目時,總仿佛看見外公站在月光里,煙斗冒出的青煙與銀河交織,將正直與擔當寫成永不褪色的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