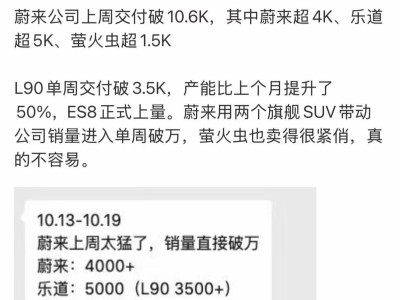北方多地近日迎來大幅降溫,部分地區氣溫驟降超10℃,哈爾濱、新疆等地甚至飄起雪花,羽絨服市場隨之進入銷售旺季。然而,消費者在選購時卻陷入糾結:價格差異懸殊的同款產品,究竟該如何選擇?是明星代言的折扣款,還是標注高充絨量的實惠款?抑或是價格低廉的“羽絨棉”替代品?雙11的促銷氛圍與對寒冷的擔憂交織,讓不少人陷入選擇焦慮。
羽絨服品牌正面臨雙重挑戰。一方面,原材料成本持續攀升,今年前9個月,白鵝毛標準毛均價雖同比漲幅收窄至3%,但仍是2020年價格的2.8倍,出廠成本中原料占比從去年的62%升至68%。另一方面,市場競爭愈發激烈,優衣庫等快時尚品牌憑借簡約設計搶占份額,蕉內等內衣品牌跨界入局,南極人、恒源祥等通過貼牌模式以低價吸引消費者,行業格局加速重塑。
平價賽道中,鴨鴨的崛起與困境頗具代表性。這個創立于1972年的老牌國貨,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占據超30%市場份額,全國門店超3000家,日銷10萬件,甚至成為“國禮”遠銷海外。然而,進入21世紀后,受國企模式拖累,鴨鴨一度瀕臨倒閉。經過多次重組,其通過直播電商實現“逆襲”:2019年至2023年,GMV從8000萬元飆升至近200億元,主力產品聚焦300-600元價格帶,精準切中大眾消費需求。但白牌工廠的涌入讓競爭白熱化,直播間里“平湖源頭工廠”“廠家直發”等標簽隨處可見,200元左右的低價產品通過繞過經銷商壓縮成本,直接擠壓品牌生存空間。
價格戰帶來的副作用逐漸顯現。隨著流量成本上升,過度依賴平臺的品牌面臨營銷費用激增與流量反噬風險。同時,原材料漲價與低價策略的矛盾導致質量問題頻發,鴨鴨近年多次被曝含絨量不達標,損害品牌形象。千元以下市場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阿迪達斯、lululemon等運動品牌,優衣庫、Zara等快時尚品牌紛紛入局,連“波司登平替”坦博爾也提交招股書,但其盈利能力卻與收入增長脫節: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營收從7.32億元增至13.02億元,凈利潤卻從0.86億元降至0.36億元,凈利率從11.7%下滑至約5.5%,“增收不增利”困境凸顯。
高端市場則呈現另一番景象。曾因“土氣”被消費者嫌棄的波司登,通過高端化轉型實現逆襲。2018年,加拿大鵝在中國市場的火爆點燃了波司登的轉型之火:同年登陸紐約時裝周,安妮·海瑟薇等明星前排看秀,價格上調30%-40%,千元以下產品占比從超五成降至不足兩成。聯名IP、明星代言、科技賦能南極科考等策略,助其營收從2018年的88.81億元增至2025年的259.02億元,凈利潤達35.14億元。但漲價勢能逐漸減弱,最新財報顯示,截至2025年3月31日,庫存周轉天數同比增加3天,存貨從31.97億元升至39.51億元,與營收增長不同步。
新興品牌高梵的崛起為高端市場注入新變量。2020年,其推出黑金鵝絨服1.0,采用匈牙利極寒地區鵝絨、日本火山巖面料,價格僅為Moncler、加拿大鵝的三分之一,卡位千元價格段。創始人吳昆明直言產品體驗優于Moncler,通過砍掉鴨絨線、主推黑色鵝絨服、強化面料研發等策略,塑造“高質價比”形象。高梵還成立巴黎、米蘭、上海三大奢研中心,融入國際時尚圈,成為首個登陸巴黎時裝周官方事件的中國鵝絨服品牌,并在巴黎頂奢店王莎瑪麗丹與LV、Moncler比鄰而居。英國皇室成員、科技大佬雷軍等名人背書,助其銷量與復購率持續提升,逐漸蠶食波司登的高端市場份額。
當前,羽絨服市場競爭焦點已從價格轉向價值。跨領域品牌入局推動產品功能化、細分化,消費者對功能屬性、美學設計及場景適用性的要求日益提高。技術迭代與智能化轉型成為行業驅動力,而2024年產品質量風波與原料成本上漲加速行業洗牌。成本攀升、信任度下滑及品牌影響力不足,擠壓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差異化競爭與個性化創新成為破局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