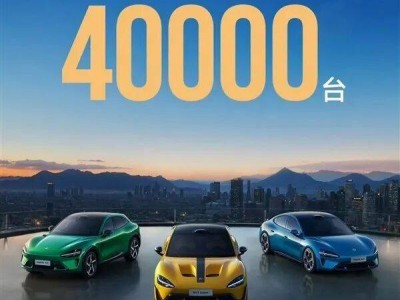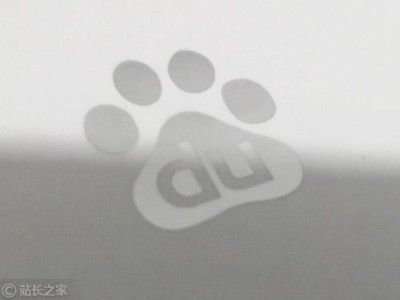早上急著去公司簽重要合同,李女士怎么也沒想到,自己的車竟在關鍵時刻“罷工”了。她插進鑰匙,用力擰到底,發動機卻只發出兩聲“咔嗒”聲,隨后便沒了動靜。儀表盤像快熄滅的燈泡一樣閃爍幾下,徹底黑了。她死死攥著方向盤,后背的汗瞬間把襯衫浸透——遲到不僅影響形象,更可能讓合作泡湯。
正慌亂時,樓下小賣部的張叔路過,敲了敲車窗:“丫頭別急,八成是電瓶樁頭銹了。”他掀開引擎蓋一角,指著電瓶正負極的接頭處,“你看,這白花花的全是銹,電流根本過不來,車能打著才怪。”李女士湊過去一看,樁頭上果然裹著一層白色粉末,手指一摸,硌得生疼,指尖還蹭黑了。
她趕緊給修配廠打電話,對方報價200元,還得等四十分鐘上門。正對著手機跺腳時,父親打來電話。聽完情況,他在電話那頭笑出聲:“傻閨女,這事兒花五塊錢就能解決。你去買包小蘇打、一瓶可樂,再從家里拿塊黃油。”李女士半信半疑,小賣部老板也勸她:“可樂黏糊糊的,洗壞了更麻煩。”可眼看時間緊迫,她只能硬著頭皮試試。
按照父親的指導,她先戴上勞保手套,翻出后備箱的扳手。父親特意叮囑:“先拆負極!就是黑線那個接頭,記住了,先負后正。”她手抖得厲害,生怕掰斷電線。螺母銹得死死的,扳手打滑好幾次才擰松。拿下接線頭的瞬間,她倒吸一口涼氣——接頭內側全是褐色銹跡,像長了霉斑。她突然想起張叔說的,上個月他鄰居就是這情況,被修配廠忽悠換了整組電瓶,花了八百多。
她把小蘇打倒進碗里,兌水攪成糊狀。父親又來電話:“可樂也行,里面有磷酸,能除銹,比小蘇打還管用。”她趕緊把可樂倒在抹布上,剛擦到樁頭,就聽見“滋滋”聲,白色粉末順著抹布往下掉。擦了兩下,抹布就黑得沒法看。她跑上樓翻出舊牙刷,蘸著可樂來回刷。泡沫順著電瓶殼流,空氣中飄著甜絲絲的酸味,倒像在做手工。
刷到露出金屬本色時,父親又提醒:“用清水沖干凈,擦干了再裝回去。裝的時候先接正極,紅的那個,別搞反了。”她特意擰緊接線頭,生怕接觸不良。最關鍵的一步來了——她挖了塊黃油,用手指仔細抹在樁頭和接線頭上,連縫隙都沒放過。黃油遇熱有點化,蹭得手指油乎乎的。“這一步才是關鍵,”父親說,“黃油能隔絕空氣和水,以后就不容易銹了。”
做完這一切,她深吸一口氣,插進鑰匙。擰到底的瞬間,發動機“嗡”的一聲啟動了,儀表盤的燈亮得刺眼,比平時還利索。低頭看表,從開始折騰到搞定,總共才十五分鐘。
下午和張叔聊天時,她才知道這毛病夏天最常見。高溫讓電瓶溫度升高,電極的絕緣層容易老化。加上她總忘關空調就熄火,電瓶負荷太大,氧化得更快。“就那層白粉末,哪怕只有一毫米厚,就能擋住電流,車自然打不著。”張叔說。
后來她特意查了下,修配廠的“專業清理”其實和她父親教的法子差不多。他們用的防腐蝕液,主要成分就是小蘇打和水,成本幾塊錢。那些賣幾十塊的保護劑,效果還不如家里的普通黃油。
上周末,她幫同事清理電瓶,對方非要用鋼絲刷使勁蹭,結果把樁頭劃得全是印子。她笑著制止:“根本不用那么費力,可樂泡兩分鐘,再用牙刷輕輕刷,銹跡就全掉了。”
現在每次洗車,她都順手擦一下電瓶樁頭。看著那層油亮亮的黃油,心里踏實多了。上周降溫,小區好幾個鄰居的車都打不著火,她帶著可樂和黃油幫他們搞定。聽著發動機啟動的聲音,她比自己賺錢還開心。
車這東西,真不用太嬌貴。很多小毛病看似嚇人,其實在家花點心思就能解決。那些動輒幾百的維修費,大多是賺的信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