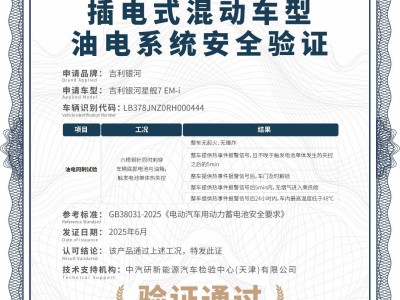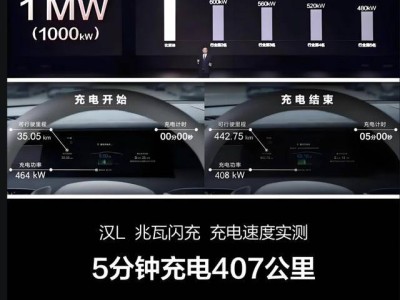在自動駕駛領域的風起云涌中,一個新的玩家悄然登場。6月23日,上海造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注冊成立,注冊資本高達近13億人民幣,其背后站著的是哈啰出行、螞蟻集團以及寧德時代這三大巨頭。
就在幾乎同一時刻,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特斯拉的Robotaxi在德州奧斯汀正式亮相,文遠知行也被曝出啟動港股IPO的消息,緊隨如祺出行上市和曹操出行遞交招股書的步伐。這個曾經被視為“未來”的領域,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資本化邁進。
哈啰此番攜手兩大產業巨擘高調進軍自動駕駛領域,并以“造父”(古代擅長駕車之人)命名,其意圖掌控自動駕駛未來的野心顯而易見。從表面上看,這幾乎是一張完美的資源拼圖:哈啰擁有數億用戶的出行場景和海量城市交通數據,螞蟻在AI大模型和復雜系統優化方面有著深厚積累,而寧德時代則手握智能滑板底盤這張降本增效的“硬件王牌”。場景、算法、硬件的“黃金三角”組合,至少在理論層面上,已經勾勒出了一條通往萬億級Robotaxi市場的快速通道。
高盛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Robotaxi市場規模預計將從2025年的5400萬美元飆升至2030年的120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超過90%。造父科技計劃于2025年第三季度在上海、成都等20個城市試點500個智能換電柜及10萬輛智能電動車。
然而,仔細探究之下,疑問也隨之浮現。哈啰在共享單車領域積累的場景優勢和數據,能否順利遷移到對技術要求更為嚴苛的四輪自動駕駛領域?螞蟻引以為傲的金融科技基因,其“敏捷”與“輕快”的特點,又能否無縫適配汽車產業對安全、可靠近乎偏執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Robotaxi的競爭格局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哈啰攜“造父”入場,面對的已不再是一片藍海,而是一個規則逐漸明確、壁壘初步形成的紅海戰場。先行者們通過經年累月的路測里程和真實運營數據,才艱難地構建起用戶對機器駕駛的安全信任,這是行業最核心也最難逾越的護城河。哈啰的這場“補課”之旅,注定不會一帆風順。
哈啰拉上螞蟻和寧德時代入局Robotaxi,看似拼出了一張近乎完美的資源版圖。這種“場景+算法+硬件”的組合,理論上能夠打通從技術研發到商業落地的閉環,怎么看都像是為Robotaxi量身定制的黃金三角。

然而,紙面上的邏輯順暢往往掩蓋了跨界落地的摩擦。今年4月三方簽署戰略協議時,“綠色兩輪出行”的目標還算務實,僅僅過了兩個月便突然轉向L4級別Robotaxi的深水區。所謂戰略協同之下,難以掩飾各自無從言明的焦慮。
哈啰的焦慮不難理解。雖然順風車訂單量不小,但低毛利的瓶頸始終難以突破;曾被寄予厚望的金融業務,在強監管和用戶信任危機的雙重擠壓下,增長空間已經受限。更關鍵的是,面對出行領域競爭對手在資本和運力上的持續加壓,哈啰急需一個更具顛覆性、更能撬動估值想象空間的新故事。Robotaxi,承載的正是這份對“未來科技出行平臺”的迫切渴望。
但從優化單車調度的區域性AI躍升至駕馭城市級復雜開放道路的L4系統,其技術跨度遠非短期資本投入所能彌補。此刻需要面對的是頭部玩家以經年累月真實路測鑄就的數據壁壘。哈啰引以為傲的海量兩輪出行數據,其價值維度聚焦于車輛分布密度、騎行熱點區域及短途通勤模式,數據動態復雜性相對有限。而Robotaxi所需的核心能力,是毫秒級應對開放道路中瞬息萬變的交通流、不可預測的極端案例,以及復雜的人-車-路實時博弈。兩者所需的數據類型、處理邏輯及算法模型,存在本質性差異。
螞蟻的入局,同樣帶有明顯的阿里基因路徑依賴。阿里系一直有著強烈的“占位焦慮”,可以承受試錯代價,但絕不能缺席潛在的戰略性賽道。螞蟻自身的技術儲備毋庸置疑,大模型、隱私計算、分布式系統優化等能力均屬頂尖。然而,金融科技的核心邏輯是風險概率的評估與管理,其安全容錯邏輯與車規級安全所要求的物理世界準則,本質上是兩種“零容忍”哲學。這種基因層面的錯位,并非簡單技術平移就能解決。
寧德時代的角色則更為微妙。作為全球動力電池的龍頭,轉身下場做自動駕駛方案商,難免會觸動車企客戶的敏感神經。當然,這并不算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寧德時代需要持續的增長敘事,智能滑板底盤既是電池技術的自然延伸,也為資本市場提供了“能源+出行”雙輪驅動的新想象。
因此,造父智能的誕生,表面上是三方資源互補的盛大聯姻,內核卻是各自戰略訴求在特定時空下的耦合:哈啰尋求估值突圍,螞蟻堅守占位法則,寧德試探邊界延伸。目標各異卻被Robotaxi的風口強行擰合在一起。
這種略帶“趕鴨子上架”式的協同,隱隱印證了戰略上的定力缺失與核心能力深耕的不足。從共享單車的幸存者到金融科技的探索者,再到如今自動駕駛的豪賭者,哈啰的擴張路徑始終走在風口浪尖。其業務版圖日益遼闊,但支撐其長期競爭力的核心技術根系,是否同步扎得足夠深廣?這恐怕是光環之下,一份未完成的作業。
Robotaxi行業的競爭肌理,在技術路線的分野中展現得淋漓盡致。百度蘿卜快跑與特斯拉代表了兩種典型路徑:前者走“激光雷達+攝像頭+毫米波雷達”的多傳感器融合路線,通過十年六代車的迭代將成本壓至20萬元;后者押注純視覺方案,試圖以算法復雜度換取硬件成本優勢。

哈啰夾在兩種路徑之間,既缺乏百度十年路測沉淀的場景庫,也沒有特斯拉芯片自研的垂直整合能力。選擇的“激光雷達為主+高規格滑板底盤”路線,本質上反映的是技術積累不足的現實妥協。
另一方面,Robotaxi商業化落地的時間窗口也在急劇收窄。2023年北京、上海劃定的L4級自動駕駛商業化運營區域,標志著行業正式從“技術驗證”轉向“規模比拼”。企業層面,百度蘿卜快跑在武漢實現的區域盈利,預計2025年全面盈利;特斯拉高調宣布入局,但業內評估其在中國達到同等運營水平仍需3-5年。反觀哈啰2026年首批落地的時間表,已經落后頭部玩家一個身位。這種滯后的代價,是路權申請進度、用戶習慣培養、基礎設施適配的全面被動。
資本市場的風向也在同步收緊。行業早已過了靠PPT融資的階段,Waymo十年燒光300億美元、Argo AI的解散,已經開始讓投資者追問技術落地的性價比。哈啰首期30億融資,按行業基準僅夠支撐兩年研發。激光雷達單價仍超400美元,千臺車隊年運維成本近億,這還未算入高昂的路測牌照與數據中心開支。
透過這場“技術-場景-資本”的三方博弈,哈啰的短板恰是行業門檻的真實寫照。在自動駕駛的金字塔中,數據與算法的頂層設計者,永遠不會是單純的場景整合者。畢竟共享單車靠的是點位爭奪,Robotaxi拼的是代碼質量,這顯然不是同一個維度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