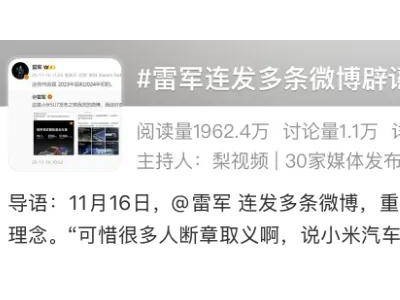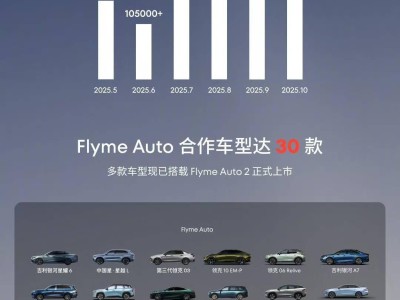日本動畫電影《≈第一部》正以驚人的速度刷新著中國內地市場的票房紀錄。上映首周末,該片總票房已逼近4億元大關,燈塔專業版預測其最終票房可能突破6億元,甚至有望超越《灌籃高手》創下的6.63億元紀錄,成為日本漫畫IP劇場版在中國內地票房最高的作品,甚至向10億元發起沖擊——這一成績遠超《火影忍者》《海賊王》等歷史級IP在中國市場的表現。
在當前電影市場整體低迷、多部國產大制作影片表現不佳的背景下,《≈第一部》的逆襲顯得尤為突出。其成功不僅源于IP本身的熱度與影片質量,更在于它成功吸引了大量非原作動畫粉絲的關注。與同期上映的《新世紀福音戰士劇場版:終》不同,《≈第一部》的觀眾反饋顯示,許多路人觀眾被其故事和情感打動,盡管認為影片節奏因回憶片段過多而略顯混亂,但仍愿意買票觀影。這種“似懂非懂卻依然愿意參與”的觀眾群體,成為推動票房持續攀升的關鍵力量。
一部帶有粉絲屬性的IP電影為何能實現如此廣泛的破圈效應?分析認為,近年來能引發廣泛討論的電影往往能精準捕捉社會情緒,成為一種社交貨幣,在傳播過程中帶來身份認同與情緒釋放。《≈第一部》作為日本近年最火的IP之一,其前作《無限列車》在日本創下票房紀錄卻未能同步引進中國內地,積累了大量未被滿足的期待。此次引進方通過線下活動制造話題,在上海、天津、深圳等地打造“痛樓”“痛地”,甚至在動漫文化相對薄弱的北京也設置了多個主題打卡點。影院方面則借鑒日本市場的“特典營銷”模式,推出不同版本的觀影場次與限定周邊,刺激粉絲多次觀影。聯名營銷層面,瑞幸推出的貼紙、亞克力立牌等周邊產品因價格爭議引發討論,進一步擴大了影片的傳播范圍。
從消費行為來看,《≈第一部》的火爆體現為一種復合型文化事件:觀眾購買的不僅是電影票,更包括線下體驗、情緒共鳴與文化參與。從影院到商場再到周邊商店,影片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消費鏈條,成為年輕人群體中的典型IP現象。這種文化狂歡的吸引力,甚至讓許多非粉絲觀眾也產生“不想錯過”的心理,主動加入觀影行列。
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影片基調與當代年輕人的精神狀態高度契合。若追溯《≈第一部》在日本走紅的原因,會發現其與日本動漫產業近十年的趨勢密切相關。與傳統熱血漫不同,該作品以大量角色的意外死亡為特點,人物命運充滿悲愴與無常。例如,劇場版中開場充滿戰意的蝴蝶忍突然被殺,這種設定打破了“死亡服務于主角成長”的常規套路,轉而呈現一種更直接的“喪感”。類似風格在《進擊的巨人》《電鋸人》《咒術回戰》等作品中均有體現,這些作品的創作者多為85后、90后,他們成長于日本經濟衰退、社會結構固化的時期,作品更關注普通人在絕望中的掙扎,而非宏大理想的追求。
這種“喪文化”的興起,與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的社會心態轉變密切相關。1995年問世的《新世紀福音戰士》已呈現類似傾向:主角碇真嗣在極度不情愿中駕駛EVA,多次逃避戰斗并否定自我,與同期《灌籃高手》中櫻木花道的熱血形象形成鮮明對比。該作品精準捕捉了日本年輕一代對未來的迷茫與抗拒,成為一代人的精神投射。三十年后,新一代創作者將這種絕望感進一步放大,而他們的作品在中國市場的走紅,則反映出兩地年輕人在精神層面的共鳴——對“努力就能逆襲”的敘事感到疲憊,在理想與現實的拉扯中尋找生存的意義。
以中國本土IP《十日終焉》為例,該作品講述一群普通人被困在“終焉之地”,每十日經歷一次生死輪回的故事。其核心設定是:無論生死,主角們都會在第十一天集體失憶并復活,重新開始。這種“明知要走向死亡卻仍選擇對抗”的敘事,與《≈第一部》的底層邏輯高度相似——在充滿無常的世界里,堅持活下去本身已成為一種反抗。這種情緒共振,正是《≈第一部》在中國市場引發熱潮的關鍵所在。
影片劇場版中,反派猗窩座的背景故事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主題。他原本是一個為父親治病而偷竊的窮苦少年,被官府鞭打時反問“正當營生買不起藥”,隨后被師父拯救卻再次遭遇命運重創,最終被迫成為鬼。這個角色的悲劇性在于,他的墮落并非自愿,而是被現實逼迫至絕境。這種“鬼未必是惡鬼,人未必是好人”的設定,正是《≈第一部》的核心魅力——它承認世界的殘酷與死亡的隨機性,卻仍留下一個問題:在這樣的世界里,你是否還愿意保持人性?答案或許悲觀,卻真實反映了當代年輕人的生存態度:明知生活艱難,仍選擇“先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