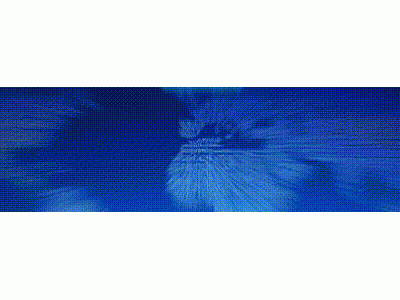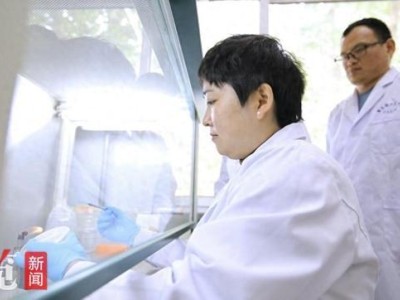“我唯一的期待就是評估時能客觀地按照郵件上說的來,比如M就是我能持續、穩定地完成工作,而不是說還要有超出預期的東西。”談及新的績效方案,字節跳動員工劉清這樣說道。
過去幾年里,隨著字節跳動持續實施“去肥增瘦”策略,績效評估逐漸向“末位淘汰”的邏輯演變,各團隊leader都背上了打出一定量“差績效”的指標,并通過排序的方式篩選出尾部員工。“Leader經常說他有多難,他有多不想給大家差的績效,但是也沒有辦法。”回憶起過往幾年的績效期,劉清說這樣的場景經常出現。
就在上周,字節跳動發布內部郵件,宣布啟動2025年半年績效評估,績效方案也迎來了“版本更新”。郵件內聲稱“此次調整主要是將績效分檔進行了升級,M、M+、E、I的規則被重新定義,旨在‘回歸價值創造本質’并構建一個包括‘穩定基線-突破激勵-頂尖認可’的三層人才發展通道。”
多年來,字節一直采取參考Google的OKR+360環評的績效模式,包括8個不同等級:
F(不及格)
I(需要改善)
M-(略有瑕疵)
M(符合預期)
M+(有時超出預期)
E(超出預期)
E+(遠超預期)
O(杰出)
在這之中,極高和極低的績效分數極少出現,絕大部分員工能接觸到的上下限在I-E之間。
每年,字節跳動各業務線會展開兩次績效評估,分為半年周期和全年周期。和其他互聯網公司一樣,績效結果與員工的年終獎金直接掛鉤,同時對于想要在公司內有更大發展空間的員工而言,獲得好績效是順利晉升的關鍵。
過去四年中,組織“去肥增瘦”一直是字節跳動的頭號管理目標之一。2021年7月,字節跳動CEO梁汝波更新個人OKR,梁汝波明確了自己新的O1(目標1)為“組織去肥增瘦,根據業務形式更新人力計劃,讓組織不膨脹和效率提升”。
就此,字節跳動“去肥增瘦”的大幕徐徐拉開,并迅速在績效環節中得以體現。在隨后的幾輪績效評估中,評估口徑逐漸發生變化,差績效指標有了更高的額度,并被強制分配到字節跳動各業務線中。

簡單解構這份績效方案,可以用三點來總結其中的新變化,M和E比例變多了;M+比例變少了;M-和I的區分度增加,郵件中特別強調,M-需要自我調整或在Leader幫助下改進,但不意味著要離開公司。其中,關于M-的口徑,被調整到一個相對“溫和”的表述。在字節跳動內部,一些員工將這份績效方案,視為公司釋放了溫和鼓勵和安撫的信號。
另一方面,一位接近字節跳動的人士表示,這次績效方案的微調,只是為了讓每個檔位被識別得更加清晰,以提升評估結果的指導性,和“去肥增瘦”沒有關系。
不過,回顧過去四年中字節對于“去肥增瘦”的執念,這份方案背后的決策者心理,似乎并不簡單。
A
這幾天,隨著新績效方案郵件公布,字節的員工們也陸續進入了新的績效評估周期,在一些團隊中,一線員工的“+1”們會在這個時間點和團隊成員“通氣”。“+1”是互聯網行業對高一級leader的稱呼,沿著這條匯報鏈的更高級別leader,以此類推會被稱為“+2”“+3”等。
劉清是字節跳動某業務線運營部門成員,他的“+1”最近專門舉行了一次組內“通氣會”,會上劉清的“+1”表示,他們所在團隊這一次的績效評估,不會有強制的差績效分布。在劉清的記憶中,這可能是2021年“去肥增瘦”戰略實施以來,績效方案針對“差績效”額度分配第一次出現松動。
“強制差績效分布,之前幾乎是半公開狀態。”楊偉就職于字節某業務線的研發部門,他表示,過去幾年中,各個團隊在績效評估時分配差績效名額的情況愈發普遍。“差績效”指M-及以下的績效等級,背上差績效不僅影響年終獎的發放數額,也會成為一些團隊勸退員工的理由。
不過,對于大部分員工而言,績效結果都是在M-、M、M+三個中間態中打出,其中,M是符合預期,M-是符合預期但略有瑕疵,M+則超越預期。也就是說,M是屬于大部分員工、占比最高的結果,而M-就已經是“差績效”范疇。隨著“差績效”成為硬指標,績效的評估標準也愈發嚴苛。

據劉清回憶,從2023年開始,績效評估中對于幾個中間態的打分理念愈發模糊。其中,原本是符合預期的“M”,也需要員工通過一些額外產出或者業務上的創新點來證明自己。“理論上你正常完成工作,就應該拿到一個正常的績效。但現在想要拿到M,就需要在業務上有一些額外的亮點。”
另一方面,原本是“略有瑕疵”的M-,卻成為一些團隊“勸退”員工的憑據,這使得原本在字節管理體系中,處于模糊地帶“末位淘汰”被拿到臺面上。今年年初的相關報道中,曾有字節內部人士透露了績效指標的分配情況。至少有7%的員工必須獲得I,15%的員工必須獲得M-,這一門檻無疑增加了員工被解雇的風險。而根據字節跳動相關政策,員工只有連續兩次獲得M-才會面臨績效改進計劃(PIP)。但在過去幾年中,一次M-就成為了危險的信號。在某些業務線,M-的比例甚至可以接近20%。
隨著“末位淘汰”理念的半公開化,大部分員工需要在業務中盡可能地證明自己的價值,進而在字節內部掀起了新一輪不同團隊、甚至不同小組間的“賽馬”。
“現在推任何項目都先問能不能降本,哪怕你做這個事的目的并不是降本。”劉清表示,持續多年的“去肥增瘦”壓力,讓降本成為了業務決策過程中的主要目標。人力資源不斷收緊的背景下,一些團隊在接新需求時也變得謹慎起來。
“績效壓力下,很多團隊從上到下開始更多地去瞄準短期收益。”楊偉表示,在更早一輪的績效方案迭代中,M+的比例曾被調高。一方面,是M-額度分配的壓力懸在每一個人頭上;而另一方面,M+比例增加帶來的刺激,也加速了團隊間的“內卷”。“大家都在業務上‘做花樣’,為了一個高績效,或者說為了一個正常的績效。”
“做花樣”在劉清口中有一個更互聯網風格的詞匯:講故事。據劉清介紹,在“去肥增瘦”的績效壓力下,很多員工如果只完成本部門業務工作,不僅拿不到一個好的績效,甚至可能會得到一個M-。這一背景下,在業務中每挖掘一些新的價值點,都要通過“講故事”贏得上游的認同,才有可能收獲一個理想的績效結果。“一些項目不一定有收益,但是可以把它包裝成有收益的樣子。”
B
在前字節HR謝燦的記憶中,2021年之前的績效策略還是一個“人性化”的版本,當時字節內部一些團隊可以不設置M-的比例,甚至在這個問題上,部門負責人也擁有一定的決策權。這一切在進入“去肥增瘦”時代后發生了變化。謝燦表示,早期字節的績效文化是“專注于和自己比”,重點在于員工的個人成長性。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績效評估留給各業務線管理崗的,只剩下三個問題:我要激勵誰、我要留誰和我不想要誰。
“把人力資源成紙面數據,這樣一方面好量化,同時可以支持決策者更好地去做判斷。”謝燦認為,強制績效分布政策的動機,是在更好地輔助管理者做決策。比如在降本增效的壓力下,一個管理者應該從哪個團隊入手進行優化,這需要管理者能夠在數據層面進行考量,并作出相應判斷。“對一些不成熟的中層管理者,公司通過這種方式強行迫使他去學會怎么做決策。”
但在和業務團隊的實際接觸中,謝燦感受到一個很明顯的變化:管理崗變焦慮了。在績效分布有了明確指標的時代,中層leader們也變得束手束腳,在持續幾年的“去肥增瘦”政策的影響下,分配“差績效”的決策影響著整個團隊的情緒。

另一方面,焦慮的不只是中層leader們,還有CEO梁汝波。時間來到2022年,梁汝波的OKR中,依舊看到“去肥增瘦”的反復刷屏。2022年7月,梁汝波更新OKR,字節跳動將根據業務形勢更新人力計劃,大幅降低2022-2023年招聘計劃,降低組織規模增速,并提升組織效率。
而在幾個月后的字節跳動全員會上,梁汝波表示,2022年公司營收增速減慢,產品DAU(日活躍用戶數量)在增長,但低于年初設定目標的預期,公司會持續地進行“去肥增瘦”。這意味著,字節在“去肥增瘦”問題上將進一步加碼,并且很快在績效層面顯現。
“每一次績效評估都會強調,要繼續收緊(評估的尺度)。”高舟曾是字節某業務運營團隊中的管理崗,在他的回憶中,績效和“去肥增瘦”的耦合,在2021年就進入了持續高壓狀態。在2022年的全年績效周期評估中,他所在業務的每個團隊都有了強制分配的“差績效”名額。事實上,字節跳動的績效評估體系分為“leader打分”、“自評打分”和“邀請同事的360度環評”三個維度,但最終的結果還是以leader們的評估為主。
“我會給一個(績效打分)草稿,然后其實最終的決定還是+2、+3來定的。”高舟表示,作為小團隊leader,他在績效評估中的話語權相對有限,很多時候他遞上去的初版方案也不會被采納。而每個部門“差績效”的指標額度,在績效評估伊始就已經確認,再由各級leader層層分配給各團隊中。“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必須得有一個(差績效),后面就可能必須得有兩個或者三個。”
背上“差績效”(一般是M-)的員工,一定會被勸退嗎?對此高舟的經驗是,一般來說“勸退”員工需要連續兩次M-(或更差的績效),但也存在只經歷一次M-,但是上游leader對某個員工表現不滿意的情況,這時就需要和當事員工“聊一下”。“‘聊一下’主要是想告訴那位同學(字節對員工的俗稱),如果不走的話可能有PIP。”
高舟口中的PIP,又稱績效管理提升計劃。該計劃主要針對績效考核未達標的員工。事實上,PIP在字節內部幾乎就是被辭退的信號,鮮有員工能通過PIP回到工作崗位。雖然名叫提升計劃,但PIP本質上是一個“勸退”員工的手段。
“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各個團隊‘卷出花’來。”談及強制差績效比例的意義,高舟表示,在“去肥增瘦”的壓力下,穩定地做業務不再是首要目標,每個團隊都需要“搶地盤”,推動更多0-1的項目進展。但卷出“花”背后,是很多團隊間在業務資源上的惡性競爭,甚至出現多個團隊“重復造輪子”的情況。
高舟進一步解構了這種狀態下的員工心理:“假如每個周期都有那么10%-20%的員工要面臨淘汰壓力,大家會發現如果在這待上幾年,被淘汰就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這樣的心理作用下,一些員工就不會有長期在這家公司從業的打算,去做一些短期業務收益大的項目顯然更有性價比。
而在管理者視角,這種“末位淘汰”的績效規則,也為團隊管理帶來巨大影響。
“一些熟悉業務的老同學可能沒犯什么錯,產出也還行,只是沒那么會匯報,沒有卷出‘花’,就要因此背上差績效。”高舟表示,“末位淘汰”對團隊進行了強制的更新換代,結果是被迫要找一些新人來取代老員工,而在業務頻繁交接的過程中,這樣的交接必然伴隨著效率的損耗。
“培養一個人,也是需要成本的,再重新招一個人也很難上手。”經歷多次業務調整的劉清,對這個問題也感同身受,他表示,2022-2023年,各團隊已經陸續勸退了一批人,經歷了多輪績效周期“沉淀”下的團隊成員,都已經是相對優秀的“精英”。這導致新的績效周期中,leader們在績效層面做決策的成本越來越高。“說直白一點,團隊中剩下的都是leader的‘心腹’了,強行分配差績效只會讓管理越來越難。”
“基層的管理崗其實很難干得太長,因為強制的績效分布,到最后總會得罪足夠多的人。”回憶起在字節帶團隊的經歷,高舟這樣說道。
C
剛剛更新績效方案中,最核心的變化在于M+比例減少/M比例增加,以及對M-進行了一次“再解釋”,郵件中強調M-代表略低于預期,需要自我調整或在Leader幫助下改進,不意味著要離開公司。相比于M-,I代表低于角色預期,不能履行好角色職責,需要做調整或離職。接下來會更清晰地識別出I及以下,不與M-混淆。
“M+少了,晉升的機會相對也少了。”楊偉表示,公司內有不少人持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反之增加比例的檔位是M和E,而獲得E需要為團隊獲得極其突出的貢獻。對于大部分員工而言,M+就是晉升的敲門磚。
“比如說你上次拿了M+,下次就肯定不能給M-,如果給M-,leader要去反復地論證。”據劉清介紹,原則上,一年中的兩次績效打分不能連跨兩個檔位,而績效的可操作性,恰恰體現在半年和全年兩個績效周期上。一位在半年績效中拿了M的員工,理論上在全年績效中同時存在打M+和M-的可能。
所以,當M的比例增加、M+比例減少,上游管理層面的可操作性也隨之增加了。

另一邊,新版績效方案中并沒有提到M-會出現比例上的變化,但是對于M-的解釋,著重提到了“不意味著要離開公司“。
“感覺(新績效方案)是在削弱末位淘汰的,相當于是減少大家的焦慮。”楊偉表示,他所在的業務橫向競爭并不激烈,“末位淘汰”的壓力相對較小。但即使如此,過去兩年中,團隊成員的焦慮情緒愈發明顯。在他看來,這一次的方案,至少在明面上做了一次理性的回歸。“讓大家預期別那么高、也別那么低,真拿了M-也別害怕。”
“我覺得字節在釋放一個信號,希望員工不要對M-這么恐慌。”站在HR視角的謝燦,在這個問題上有著同樣的判斷。在他看來,字節方面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進一步控制成本,同時穩住員工的情緒和積極性。“公司既需要更多的M-降低薪資部分的支出,同時也相當于表個態度,得到M-并不意味著要裁掉你。”
“在以前M-就已經是一個比較不好的結果了,而I基本意味著‘再無翻身可能’。”在劉清眼中,新方案中的M-有一點變寬松的跡象,作為“差績效”的嚴重程度有所削弱,但劉清并不認為這一動作會有帶來多少積極影響。“想在字節待下去,就不能被斷后路,從這個角度講M-影響還是很大。”
劉清的判斷來自于字節的相關人事政策的約束,據了解,一旦字節員工背上M-的績效,即使不被勸退,但也無法主動轉去其他業務線。根據字節的轉崗政策“活水”規定,員工申請活水需要至少M的績效。事實上,一旦履歷出現了一次M-,在之后的字節生涯中都會成為一個要反復解釋的因素。
“甚至以后離職后想要再回流(離職后再入職字節)都很難,一次M-需要很多次的好成績才能‘洗刷’掉。”對于M-的長期影響,劉清這樣解釋道。
從HR視角來看,謝燦認為,持續的“去肥增瘦”的壓力,的確讓很多業務線變得更偏好短期收益,這導致中層和基層管理者很難培養成有長期視角、有戰略眼光的這種領導者。“這個時候可能就需要更上層的管理者有足夠的管理經驗和長期的視野,但這就是另外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了。”
“現在沒有那么多高速增長的業務要做,如果是想守住存量業務的話,還是需要有一些人來踏踏實實地做事情。”在高舟看來,新績效方案的調整,源于字節在內的互聯網大廠,在當前業務場景下的一些態度轉變。“(績效方案調整)初衷肯定是這樣的,但是考慮到組織的慣性,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可能沒有這么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