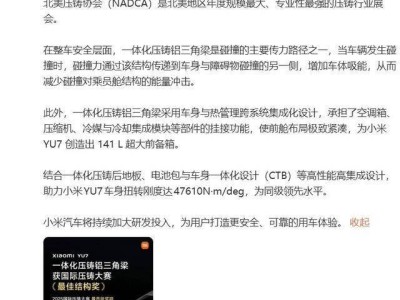站在鄭州黃河文化公園的觀景臺上,極目遠眺,平靜的河面泛著粼粼波光,兩岸的生態林帶郁郁蔥蔥,飛鳥在濕地間自在翱翔。這幅生機勃勃的畫面,正是黃河從“水患之河”走向“安瀾之河”的生動寫照。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始終承載著“歲歲安瀾”的美好愿景,而今,這一愿景正在河南大地上逐步變為現實。

黃河防汛,曾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河道工程的細微變化,尤其是水下固堤石的移位或松動,往往難以被及時發現。過去,人工巡查不僅耗時耗力,還容易遺漏隱患。如今,在河南黃河段,一批高科技“哨兵”正24小時守護著河道安全。在鄭州黃河防汛前線指揮中心,惠濟區委智慧城市運行辦公室副主任張釗展示了一款形似石頭的高精度傳感器。“別看它不起眼,卻能實時監測固堤石的微小位移,一旦有異常,數據會立即上傳。”他介紹道。目前,河南黃河段已布設了1962個這樣的“智能哨兵”,配合無人機巡查、AI視頻監控和“智能測艇”,形成了“天上看、地上巡、水里探”的立體監測網絡。工作人員只需輕點手機或電腦,就能隨時掌握黃河的動態,“掌上巡河”已成為現實。
在鄭州市區的“模型黃河”實驗基地,一條800米長的模擬河道靜靜流淌。這里精準復刻了黃河下游的游蕩性河段和泥沙淤積區,能夠模擬不同強度的降雨場景。黃河水利科學研究院泥沙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夏修杰表示:“每年汛期前,我們都會進行大洪水演進模擬試驗,為實際防汛提供科學依據。”這種“未雨綢繆”的演練,依托自主研發的智能設備,為黃河防汛筑起了一道“科技堤壩”。
小浪底水利樞紐,堪稱科技治黃的“重頭戲”。這座掌控黃河92%流域面積、91%徑流量和近100%泥沙的“超級工程”,通過遍布樞紐的傳感器,將現實中的小浪底完整“搬”進了電腦。調水調沙時,系統只需輸入參數,就能自動計算出最優方案,將“經驗調度”轉變為“數據驅動”。小浪底管理中心開發公司正高級工程師李立剛透露,自2002年至今,依托數字孿生系統與智能設備,小浪底已成功開展31次調水調沙,黃河下游主河道的底部平均被“挖”深了3.1米,每秒過水能力增加了近兩倍。
黃河的生態蛻變,同樣令人矚目。蘭考東壩頭黃河灣風景區,曾是“風沙、內澇、鹽堿”三害肆虐之地。1962年,焦裕祿帶領群眾“追風口、探流沙”,開啟了治沙的序幕。如今,52公里的生態林帶像綠色屏障般護住河岸,31公里的生態步道串起沿途風光,100多種植物扎根生長,160多種鳥類在此安家,昔日的“三害之地”已變成“鳥類天堂”。
三門峽庫區的生態故事同樣精彩。作為守護黃河安瀾的重要工程,三門峽水庫不僅發揮了防洪、防凌的作用,還滋養出一片廣袤的濕地。每年上萬只白天鵝來此越冬,讓三門峽贏得了“天鵝之城”的美譽。三門峽中流砥柱博物館講解員介紹:“過去黃河斷流時,濕地生態惡化,現在通過水庫調蓄和水量統一調度,生物多樣性越來越豐富。”目前,庫區周邊鳥類已從175種增加到315種,占河南省鳥類總數的82.5%。

水利工程是守護黃河安瀾的“壓艙石”。在河南黃河岸,500多公里的標準化堤防像一道“鋼鐵長城”蜿蜒鋪開,每一段都能抵御花園口每秒22000立方米的洪水沖擊。50多處新續建的河道整治工程、40多處翻新加固的險工與防護壩,將“地上懸河”的游蕩河勢牢牢鎖住。開封黑崗口黃河法治文化廣場,一棵挺拔的福桐見證了水利工程的變遷。站在河勢觀測臺遠眺,1.5公里寬的黃河水面上,控導工程像沉穩的“河脈調節器”,將河道捋得規規矩矩。開封第一河務局局長江浩感慨:“過去這里是出了名的‘險段’,現在有了控導工程,黃河主槽基本穩定,防汛壓力小多了。”
黑崗口引黃渠首閘,則藏著“害河變利河”的故事。這座1957年建成的涵閘,歷經三次改建,如今每年能引1.3億立方米黃河水,既供開封市民飲水、工業用水,又灌溉了農田,連城市河流的生態補水都靠它,成了實實在在的“民生閘”。
鄭州黃河文化公園的“三橋匯”,像一部濃縮的治黃工程史。1903年的鄭州黃河鐵路橋,廢棄的橋墩上還留著近代治黃的艱難印記;1958年的鄭州黃河公路橋,帶著新中國治黃起步時的踏實與探索;2010年通車的鄭新黃河大橋,以舒展的斜拉橋身姿,亮出當代中國的工程底氣。三座橋并排橫跨黃河,不僅是交通發展的縮影,更是河南治黃從“苦守”到“巧治”的生動見證。
從“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苦難記憶,到“伏秋大汛不決口,地上懸河不抬高”的安瀾現狀,河南治黃的每一步都凝聚著智慧與汗水。如今漫步黃河岸邊,昔日讓人憂心的“水患之河”,早已變成滋養百姓、孕育希望的“幸福之河”。滔滔黃河奔涌向前,千百年的安瀾夢,正一步步照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