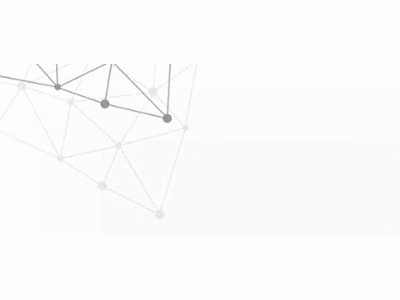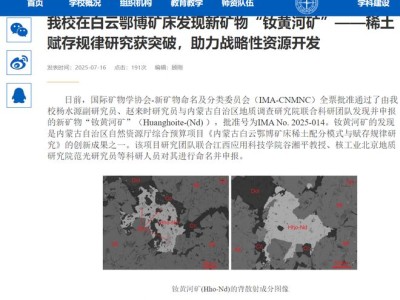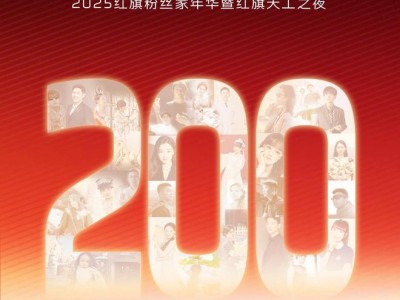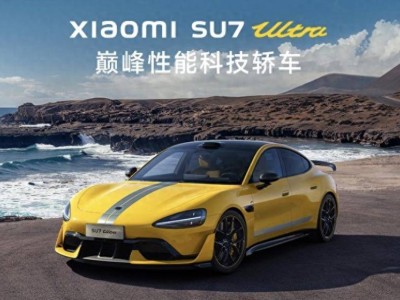1975年,美國紐約州柯達公司研發(fā)實驗室里,一位年輕工程師完成了一項“可愛”的發(fā)明。
那是一個重約3.6公斤、大小如烤面包機的裝置,能在23秒內(nèi),將一張100x100像素的黑白影像記錄到一盤磁帶上。這是世界上第一臺數(shù)碼相機。
然而管理層的反應卻是“這很可愛,但別告訴任何人。”
管理層的恐懼不難理解。柯達的商業(yè)帝國建立在膠片和相紙的銷售之上。新發(fā)明,從根本上威脅了這一切。
于是,這項革命性技術被雪藏了,這也導致了柯達灰暗的未來。2012年,它正式申請破產(chǎn)保護。
半個世紀后,當我們揭開這面被塵封的鏡子,把目光投向蘋果帝國時,一個問題開始浮現(xiàn):在AI浪潮席卷全球的當下,蘋果是否正經(jīng)歷它的“柯達時刻”?
作者 | 張豫婷
編輯 | 方遠
“自我革命”的恐懼
讓我們先把目光從柯達移開,轉向另一個更為切近的帝國,那便是諾基亞。
在2007年第一代iPhone發(fā)布時,諾基亞是無可爭議的手機霸主,市場份額達40.5%。諾基亞的衰落,常被簡單歸咎于“未能創(chuàng)新”。
然而,事實遠比這復雜。深入剖析其敗因,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個與柯達驚人相似的邏輯:諾基亞并非沒有創(chuàng)新,而是被基于塞班的封閉體系,給牢牢鎖死了。
塞班系統(tǒng)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每開發(fā)一款新型號手機,工程師都需要重寫大量底層代碼。這導致諾基亞的新品推出周期,要比競爭對手滯后6到9個月。
更致命的是,在2008年,當蘋果以開放姿態(tài)擁抱第三方開發(fā)者時,諾基亞卻出于維持系統(tǒng)控制權的考慮,拒絕為開發(fā)者開放關鍵接口。
最終,諾基亞錯失了轉向Android或徹底改造自身系統(tǒng)的最佳時機,他們專注于硬件的迭代和利潤,卻忽視了戰(zhàn)場已經(jīng)轉移到了軟件生態(tài)。
現(xiàn)在,讓我們回到2025年的蘋果。
蘋果發(fā)布的Apple Intelligence,被許多觀察家視為“慢半拍”的AI戰(zhàn)略。

它強調(diào)極致的隱私保護和系統(tǒng)級整合,大部分運算在本地完成,這需要M1及以上級別的強大芯片支持。這是蘋果的傳統(tǒng)優(yōu)勢:軟硬件一體化的完美體現(xiàn)。
數(shù)據(jù)顯示,2024年,iPhone硬件收入仍占蘋果總營收的51.45%,而AI,尤其是生成式AI,其本質是一種軟件和服務。這就帶來了一個深刻的商業(yè)模式?jīng)_突:
首先是定價權的博弈,微軟、Google的AI服務,大多采用每月20美元左右的訂閱制。如果蘋果也采用類似的模式,用戶會問:
如果我花錢訂閱了強大的AI服務,為什么還需要每年更換最新、最貴的iPhone?
其次,蘋果的封閉生態(tài)既是護城河,也是擁抱AI革命的掣肘。一份內(nèi)部評估報告顯示,要讓Siri達到現(xiàn)代AI助手的水平,需要重構30%的底層代碼,這讓蘋果投鼠忌器。
這種兩難,或將成為蘋果的“柯達時刻”。
人心思變
在新技術沖擊同時,人員的變動,同樣在加速帝國黃昏。

一個帝國的黃昏,往往始于內(nèi)部人心的浮動。
蘋果2024-2025年關鍵離職名單,如同一份令人警醒的備忘錄。
2024年10月,上任不到2年的首席人力官宣布離職,高管的接連變動,在一個將“人才”視為核心資產(chǎn)的公司是極不尋常的。它暴露了蘋果在全球AI人才爭奪戰(zhàn)中的窘境。
2025年1月,首席財務官 Luca Maestri離開,當時蘋果正面臨AI巨額投入的預算壓力,財務大管家的更迭,加劇了外界對其AI投入決心的疑慮。
7月8日,曾被視為庫克的潛在接班人的Jeff Williams 卸任,作為運營和供應鏈的靈魂人物,他的退休,讓蘋果的未來領導層充滿了更多不確定性。
更令人擔憂的數(shù)據(jù)是:2024年,蘋果AI團隊的離職率高達34%,顯著高于谷歌的15.1%。而這些頂尖人才中,有63%選擇加入了OpenAI、Anthropic等更純粹、更激進的AI初創(chuàng)公司。
這面鏡子,再次映照出諾基亞的影子。在諾基亞的最后歲月里,許多富有才華的工程師和設計師因無法忍受公司的官僚主義而出走,加入了蘋果和谷歌。
高管的“換血”和人才的流失,是蘋果內(nèi)部“戰(zhàn)略焦慮”的外部投射。
這種焦慮的核心,與諾基亞當年如出一轍:公司龐大的身軀,在面對顛覆性技術時,顯得遲緩而笨重。
黃昏降臨
當然,將今天的蘋果與當年的諾基亞簡單類比,也可能犯下刻舟求劍的錯誤。我們需要冷靜分析,AI革命對蘋果的沖擊,與智能手機革命對諾基亞的沖擊,是否在同一個量級?

智能手機用了9年時間,才在全球達到40%的普及率。而生成式AI,僅用了不到3年,滲透率就已達到35%。AI的傳播速度和影響力,遠超上一輪技術革命。
在成本維度,當年,構建一個智能手機生態(tài)(如iOS或Android)的成本約為120億美元。而今天,一個科技巨頭要想在AI領域建立領導地位,投入預計將超過200億美元。
這意味著,AI革命的顛覆性可能比智能手機革命更為劇烈,留給傳統(tǒng)巨頭的反應窗口期也更短。
AI對蘋果的挑戰(zhàn),可能不是出現(xiàn)一個“更好的iPhone”,而是讓“手機”這個載體本身變得不再那么重要。
當AI助手可以跨設備、無縫地為我們處理一切事務時,我們對特定硬件品牌的忠誠度是否會下降?這才是蘋果最深層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