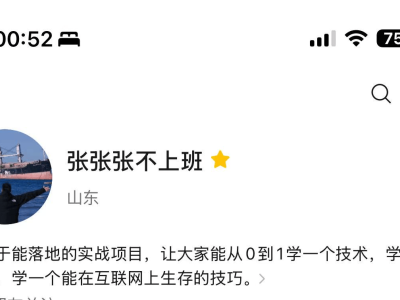可控核聚變被視為解決人類能源危機的終極方案,但關于其燃料氚的稀缺性,公眾中常流傳著一種擔憂——全球天然氚儲量僅兩三公斤,是否足以支撐核聚變技術的規模化應用?這種疑慮背后,實則是對核聚變燃料循環機制的誤解。科學家指出,現代聚變堆設計已突破天然氚的限制,通過“自產自銷”模式實現燃料可持續供應。
氚是氫的放射性同位素,原子核內含一個質子和兩個中子,半衰期僅12.3年。天然氚主要存在于深層海水與地殼中,總量稀少且提取成本高昂,每克價格堪比黃金。然而,聚變堆的燃料設計并未依賴這一“天然庫存”,而是構建了閉環循環體系:聚變反應釋放的高能中子轟擊堆芯中的鋰-6同位素,通過核嬗變反應生成氚。這一過程如同“點石成金”,將儲量豐富的鋰轉化為聚變燃料。
鋰資源的豐沛程度遠超想象。全球已探明鋰儲量超過2600萬噸,廣泛分布于鹽湖、礦石及黏土中。以當前技術,1噸鋰可生產約6.6公斤氚,而一座百萬千瓦級聚變電站年耗氚量僅約500克。更關鍵的是,聚變堆啟動初期所需的少量氚,可由核電站副產品或歷史核試驗遺留物提供——這些“存量燃料”足夠支撐首批聚變裝置的點火需求。
“這就像用火柴點燃篝火,火柴雖小,但篝火燃燒產生的熱量足以持續烘烤木材。”核物理學家以通俗比喻解釋燃料循環原理。聚變反應中,氘(另一種氫同位素,海水中的儲量足夠人類使用數億年)與氚結合釋放能量,同時生成的中子持續催化鋰轉化為氚,形成“燃燒-再生”的動態平衡。即使考慮設備損耗與效率問題,現有鋰儲量仍可支撐聚變能源數百年需求。
技術層面,聚變堆對鋰的提取要求遠低于電池行業。當前鋰產業主要依賴高純度碳酸鋰,而聚變燃料僅需天然鋰礦石或鹵水中的鋰-6同位素(占比約7.5%),分離技術難度與成本均顯著降低。科學家正在研發更高效的鋰增殖層材料,未來可能實現氚產率的翻倍提升。
公眾對氚短缺的擔憂,某種程度上源于對核技術復雜性的低估。正如火箭工程師會精確計算每一克燃料,聚變科學家早已將燃料循環納入整體設計框架。從鋰的開采到氚的再生,每個環節均經過數學建模與實驗驗證,確保系統穩定性。事實上,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的燃料供應方案中,天然氚僅占初始需求的5%,其余均依賴中子嬗變自產。
值得補充的是,氚并非聚變能源的唯一路徑。氘-氘聚變反應雖需更高溫度,但完全擺脫了對氚的依賴,且海水中的氘資源近乎無限。隨著高溫超導材料與等離子體控制技術的突破,未來聚變堆可能直接采用氘-氘燃料,徹底消除燃料供應顧慮。
從石油危機到可再生能源崛起,人類能源史始終是一部“破局史”。當聚變之火真正點燃時,我們或許將面臨一個意想不到的“煩惱”:如何為過于廉價的清潔能源制定合理的定價機制。這場能源革命的終點,可能比多數人想象的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