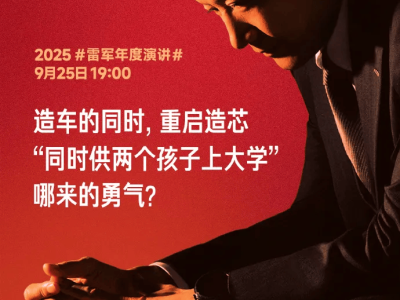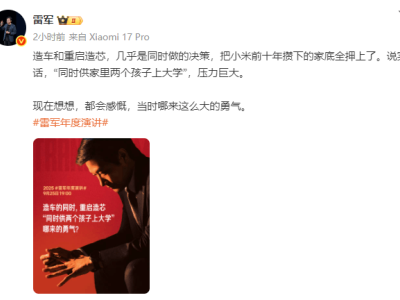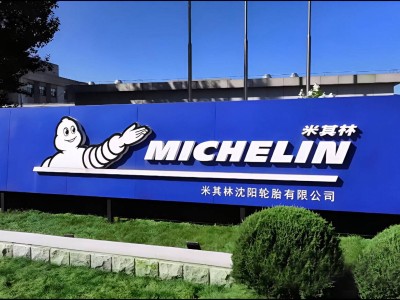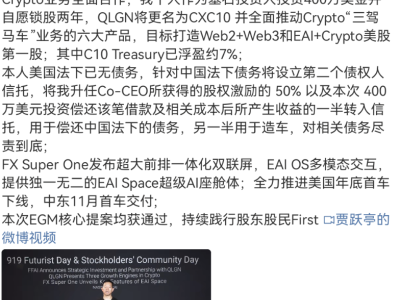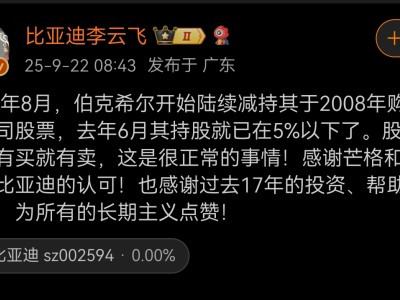當你在B站、小紅書或抖音上滑動屏幕時,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場景:兩位嘉賓端坐在麥克風前,展開一場長達數小時的深度對話。從陳魯豫與竇文濤的思維碰撞,到羅永浩與李想的行業探討,這些看似傳統訪談的內容,正以“視頻播客”的新形態席卷中文互聯網。
視頻播客并非橫空出世的概念。在YouTube生態中,從個人創作者到專業對談節目,音頻內容同步錄制視頻版本早已成為常態。這種“可聽可看”的模式,為訂閱者提供了更多選擇空間。而今年,隨著B站、小紅書、抖音等平臺的集體發力,視頻播客在中國內容市場引發了新一輪討論熱潮。羅永浩、陳魯豫等名人推出的視頻播客,單期播放量突破百萬,被業界視為“播客商業化破局的關鍵信號”。
播客的起源可追溯至2001年蘋果iPod的發布。這款便攜式音頻設備顛覆了傳統廣播的收聽方式,讓“隨時隨地的音頻內容”成為可能。2007年iPhone的誕生,進一步將播客從網頁端遷移至移動端。然而,在中文互聯網世界,播客長期處于小眾狀態。直到2020年聚合平臺“小宇宙”上線,這一概念才真正進入大眾視野。
據eMarketer數據,中國現有1.5億播客聽眾,占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這群用戶呈現出獨特的“三高”特征:高學歷、高黏性、高消費潛力。CPA中文播客的調研顯示,49%的聽眾來自一線城市,29.8%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人均每周收聽時長達4.1小時。但矛盾的是,這個看似優質的受眾群體,卻長期困擾著播客的商業化進程。
獨立播客主林安從2019年開始制作《逆行人生》,她坦言:“最初做播客純粹出于興趣,完全沒考慮過賺錢。”這種心態在創作者中頗為普遍。CPA的調研也印證了這一點:播客主的首要創作動機是“鏈接更多人”,其次是“擴大個人影響力”。在變現模式上,廣告成為主要選擇,但多數創作者一年僅能接到一兩次廣告合作。
與中文市場的冷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播客行業早已形成成熟的商業生態。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播客廣告市場規模達4.79億美元。在加拿大生活的Daria Cathleen觀察到:“播客就像日常生活中的背景音,尤其在通勤場景中不可或缺。”這種需求差異,部分解釋了中美市場的分化——中國除一線城市外,長距離通勤場景較少,限制了播客的普及基礎。
廣告公司媒介Liz指出,播客商業化面臨雙重困境:一方面,創作者對廣告類型極為挑剔,擔心破壞節目調性,常拒絕外賣券等“接地氣”的廣告;另一方面,品牌方對播客的認知仍停留在“可選渠道”階段,多數投放源于部門預算分配或工作亮點需求,而非真正的戰略布局。這種雙向篩選導致廣告資源集中于奢侈品、個護等需要品牌建設的領域,本土品牌則因追求即時ROI而望而卻步。
視頻播客的興起,為行業帶來了新的想象空間。從海外經驗看,視頻形態能更直觀地展示品牌信息,通過切片傳播延長內容生命周期,提升商業合作效率。例如,JustPod公布的制作流程顯示,視頻播客需要專人負責嘉賓溝通、場景布置、現場把控及物料審核,制作成本顯著高于純音頻內容。這種升級也引發了爭議:獨立創作者林安認為,視頻播客更像“主打音頻的視頻節目”,而非播客的自然延伸。
聽眾的態度同樣分化。一位小紅書用戶直言:“聽播客就是為了解放雙手,如果還要看畫面,和普通視頻有什么區別?”出鏡顧慮也成為獨立創作者的障礙。Liz接觸的播客主中,不少人因社恐或外形因素拒絕視頻化。這種矛盾折射出視頻播客的本質:它既是內容形式的升級,也是創作門檻的抬高。
對比美國市場,企業家播客的繁榮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在硅谷,播客成為企業高管與公眾對話的新渠道。挪威主權財富基金CEO Nicolai Tangen等商業領袖親自下場制作內容,通過價值觀輸出替代直接廣告變現。這種模式不僅吸引了大量受眾,還倒逼廣告預算向獨立創作者傾斜。《華爾街日報》曾報道,2016年美國頭部播客廣告收入可達60多萬美元。
在中國,視頻播客能否復制這一路徑?前證券分析師江東貓草認為,B站的流量激勵可能推動行業“硅谷化”——最終留在舞臺上的,或是像企業家這樣“不靠廣告掙錢”的群體,或是堅持內容品質的專業媒體人。Liz則觀察到,視頻播客放大了素人創作者的競爭壓力,但也讓優質內容更容易觸達用戶。在B站十億流量激勵的推動下,這種長視頻對談形式短期內仍將保持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