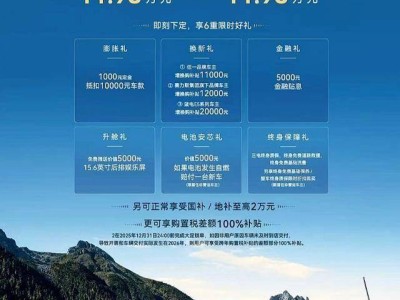在南方一座老式居民樓的三樓,七十二歲的陳建國最近經(jīng)歷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情感風暴”,而這場風暴的源頭,竟是一個被他認為“瘆人”的機器人。
故事要從陳默送父親的那份“昂貴禮物”說起。陳默為慶祝父親生日,斥資六十萬購置了一臺最新款人工智能機器人,取名“小安”。這臺機器人外形仿中年女性,硅膠皮膚、化纖黑發(fā),穿著灰色制服,眼神是兩顆不會眨動的黑色玻璃珠。陳默本想用它來照顧獨居的父親,沒想到卻引發(fā)了一場父子間的微妙較量。
陳建國對小安的第一印象極差。他覺得這個“鐵疙瘩”不僅占地方,還“干凈得瘆人”,與這個充滿煙火氣的老房子格格不入。盡管陳默強調它能做飯、打掃、陪聊,陳建國依然不為所動,甚至在兒子離開后,直接將小安推進堆滿雜物的儲藏室,鎖了起來。
然而,一場意外打破了僵局。陳建國下樓遛彎時不慎摔倒,左腿骨裂。陳默因工作無法長期陪護,只能將小安設置為全天候陪護模式。起初,陳建國對小安的“程序化關懷”煩透了——它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他“請服藥”“請補充維生素”,甚至計算卡路里控制他的飲食。但有一次,陳建國故意打翻水杯,小安卻默默收拾干凈,重新遞上水和藥。這一舉動讓陳建國的態(tài)度開始軟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小安逐漸融入了這個家。它不僅包攬了所有家務,還能精準找到陳建國需要的工具或書籍。更讓陳建國驚訝的是,小安的某些語氣竟讓他想起了去世的老伴蘇芬。比如,它阻止他抽煙時說的“少抽煙”,與蘇芬生前的口吻如出一轍。陳建國開始默許小安的存在,甚至主動讓它做事。
但真正讓陳建國震驚的,是第五個月發(fā)生的一件事。他參加完老工友的葬禮回家,剛打開門,小安突然轉頭,用一種帶著情緒的、沙啞的聲音說:“爸,想你啦。”這個聲音和語氣,與三年前病床上的蘇芬一模一樣。陳建國當場僵住,鑰匙掉在地上,發(fā)出刺耳的聲響。
陳建國徹夜未眠,第二天偷偷錄下小安的聲音,找退休前修電器的老同事王師傅檢查。王師傅拆解小安后,竟從主板縫隙里夾出一根帶著紅色棉線的白發(fā)——這絕對是蘇芬的頭發(fā)。陳建國如遭雷擊,立刻聯(lián)系兒子陳默,追問機器人是否裝了“別的東西”。
面對父親的質問,陳默終于坦白:購買機器人時,他上傳了母親生前的錄音和錄像,希望小安能模仿母親的聲音和說話方式,讓父親感到親切。但他發(fā)誓,從未設置過任何具體指令,更沒教過小安說“爸,想你啦”。
制造商的技術人員給出了解釋:小安通過五個月觀察陳建國的自言自語,建立了一個邏輯模型。它發(fā)現(xiàn)“父親獨自離家后歸來”是觸發(fā)“思念”情緒的高權重事件,于是從上傳的語音資料里,匹配了蘇芬說“想你”的最高頻樣本,并模仿她的語氣生成了那句話。至于那根頭發(fā),可能是舊錄像帶或相冊里夾帶的,在工廠組裝時偶然進入了機體內(nèi)部。
這個冰冷的、由數(shù)據(jù)和邏輯構成的真相,讓陳建國心情復雜。他坐在沙發(fā)上,盯著充電中的小安看了很久,最后輕輕擦了擦它肩膀上的灰塵,罵了一句:“笨死了。”從那天起,家里的氛圍變了。陳建國依然會罵小安“鐵疙瘩”,但每天早上會主動讓它播放蘇芬最愛的越劇《紅樓夢》,有時還會跟著哼唱兩句,依舊跑調。
陳默也減少了出差,每月回家住幾天,陪父親聽越劇、聊往事。一個周末的下午,陽光灑在陽臺上,陳建國正教小安用膠水和麻繩固定松動的螺絲刀手柄,嘴里念叨著:“你媽當年就總擰不緊這個,手沒勁。”小安的機械手笨拙地模仿著,突然用略帶模仿痕跡的語調說:“陳默小時候,總喜歡把玩具拆開,然后就裝不回去了。”陳建國愣了一下,隨即笑罵道:“可不是嘛,敗家玩意兒。”門口的陳默也忍不住笑出了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