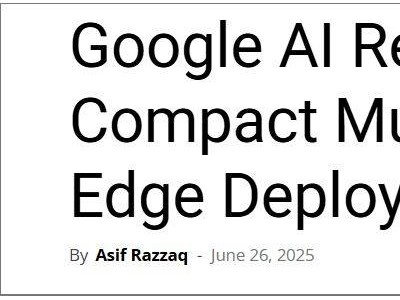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認知革命一直是推動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從七萬年前智人通過虛構故事實現認知飛躍,到一萬年前農業革命讓我們定居農耕,再到三百年前科學革命引領我們成為地球主宰,每一次變革都深刻地重塑了人類社會。而今,我們正站在第三次認知革命的門檻上,這一次,引領變革的不再僅僅是人類。
近年來,人工智能(AI)技術的迅猛發展,特別是像ChatGPT這樣的大型語言模型的誕生,標志著人類創造出了能夠理解和生成語言的機器。這一突破性進展,不僅讓語言這一人類獨有的關鍵能力不再成為專屬,更開啟了新的“宗教儀式”。人們每天通過AI對話界面提問、接收回應,這一行為正在逐漸演變成全球數十億人的日常習慣。AI的全知假象、永恒耐心、個性化回應以及即時性,讓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新的“神諭”。
隨著AI技術的普及,社會分化也在悄然發生。技術原教旨主義者堅信通用人工智能(AGI)即將到來,人類將迎來升華或滅亡的轉折點;實用主義者則將AI視為工具,以提高效率為首要目標;而盧德分子2.0則警告AI可能帶來的危險,擔心人類會創造出自己的掘墓人。這三種不同的態度,反映了人們對AI技術未來發展的不同預期和擔憂。
在AI革命的影響下,新的社會結構正在形成。科技巨頭如英偉達、OpenAI、谷歌、微軟和Anthropic等,成為了新時代的“王朝”,他們控制著數據、算力和算法這一新的基礎設施。而由此產生的算法貴族、提示工程師、數據勞工和數字農民等社會階層,則揭示了AI技術帶來的深刻社會變革。數據勞工在肯尼亞、菲律賓和印度的辦公室里,為AI準備“食物”,他們的勞動支撐著AI的智能,卻往往被遺忘在光鮮的技術敘事之外。
AI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引發了關于意識和智能的深刻討論。GPT-4等AI模型能夠寫出感人的詩歌、解決復雜的數學問題、進行哲學辯論,但卻不具備“感動”、“理解”和“思考”的主觀感受。這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智能行為可能不需要意識。無意識的智能正在接管越來越多原本屬于人類的領域,從醫療診斷到法律咨詢,從藝術創作到科學研究,AI正在證明完成任務不需要理解,模仿不需要體驗。這意味著,意識的特權正在瓦解。
在人文主義主導意識形態的過去300年里,個體被奉為神圣,人類體驗是意義的源泉,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基礎,理性是通向真理的道路。然而,新的意識形態——數據主義正在崛起。它相信宇宙由數據流組成,生命是數據處理的算法,價值來自于對數據流的貢獻,自由流動的數據是最高的善。數據主義的第一教義是連接即美德,第二教義是算法知道更好,第三教義是處理即存在。在數據主義的影響下,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早晨醒來查看手機通知到晚上在算法推薦的視頻中入睡,一切都圍繞著數據的生產和交換。
AI革命帶來的失業恐慌也不容忽視。與以往的自動化替代體力勞動不同,AI正在替代認知勞動,這是人類自以為獨特的領域。律師、會計師、分析師和設計師等白領職業正在被AI蠶食,創意工作的門檻降低、產量爆炸但獨特性消失。然而,新的工作形態也在悄然出現,如AI督導員、體驗設計師、人際連接師和數字考古學家等,這些職業需要技術知識、哲學思考、倫理判斷和人文關懷。
AI革命還可能改變人類對于死亡和永生的認知。隨著數字遺產的演進,從社交媒體賬號、郵件和照片到AI模擬的對話風格,再到全息投影和意識上傳,人類或許能夠實現數字永生。然而,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數字永生可能創造終極的不平等,富人擁有專屬服務器和無限算力,而窮人只能承受壓縮版本和低分辨率的永生。在數字世界中,意識可能遵循新的進化規律,更高效的思維模式被復制,無用的記憶被淘汰,成功的人格特質被分享。
隨著AI技術的不斷發展,全新的數字生命形式可能出現,如AI原生的意識形態、人機混合的新物種和純粹的信息生命體等。這些超越我們理解的存在形式,將如何與人類共存、如何影響人類社會,都是我們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我們或許已經是賽博格(人機結合體),只是假肢不在身體里,而在口袋中。智能手機、AI助手等智能設備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未來它們將如何進一步融入我們的生活、改變我們的社會,值得我們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