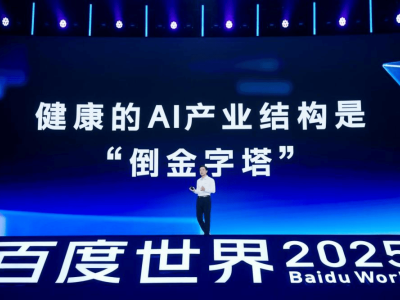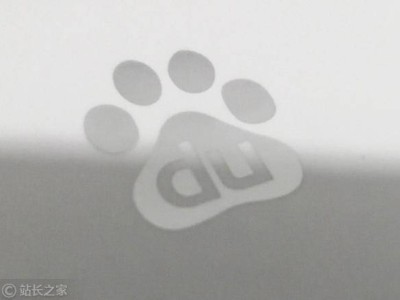國慶檔電影市場的冷清與旅游業的火熱形成鮮明對比。今年國慶期間,盡管多部明星云集的影片如《志愿軍:浴血和平》《三國的星空》等上映,但票房表現普遍低迷,單片最高票房未突破5億元,整個檔期總票房不足19億元,觀影人次較往年大幅下滑。與此同時,國內旅游市場卻呈現爆發式增長,山東旅游訂單量同比增長22%,四川涼山州游客數量激增21.56%,高速公路車流如織,顯示出消費需求并未消失,而是轉移到了其他領域。
在電影市場遇冷的背景下,短劇行業卻異軍突起。2025年上半年,短劇市場迎來爆發式增長,頭部作品如《十八歲太奶奶駕到》上線首日熱度破億,4天播放量超10億,創下平臺最快紀錄。另一部作品《一品布衣》結合穿越與權謀元素,以電影級制作水準獲得觀眾高度認可。數據顯示,今年暑期檔頭部短劇貢獻了311億次觀看,甚至超越了傳統電視劇的表現,短劇熱度值破億已成為常態。
短劇行業的崛起吸引了眾多電影人轉型。周星馳、賈樟柯、王晶等知名導演,以及舒暢、李若彤、李沐宸等演員紛紛涉足短劇領域。盡管轉型意味著片酬大幅縮水——例如演員李沐宸在電視劇市場的單集片酬約30萬元,而在短劇領域僅數萬元——但電影市場的萎縮迫使從業者尋求新出路。2024年電影總票房僅為425億元,較2023年縮水超100億元,觀影人次跌幅超過23%,非節假日時段部分影院場均觀影人次不足5人,半數以上影視上市公司持續虧損。
電影市場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資本投資減少是首要因素,華誼兄弟CEO王中磊曾提出“2億預算紅線”,超過此預算的項目大概率虧本,導致大制作電影數量銳減。而觀眾前往影院的主要動機之一——觀看大制作影片——因此受到抑制。電影行業上游存在復雜的交叉投資現象,多家公司通過資本運作將電影成本轉化為金融產品,一級市場向二級市場轉讓,甚至涉及灰色產業,無形中推高了制作成本。如今,隨著互聯網資本介入,電影行業監管更加透明,票房實時統計使得造假難度增加,資本炒作空間被壓縮。
相比之下,短劇市場的增量空間顯著。資本開始涌入短劇領域,東方財富Choice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短劇互動游戲指數累計上漲5.7%,相關概念股表現亮眼,多家上市公司股價漲幅超過40%。短劇的商業生態對導演和演員更為友好,拍攝周期短、效率高,一部10分鐘的短劇通常3天即可完成,演員可在相同時間內參與更多作品,提升總收入。短劇演員的流量變現能力突出,例如王星辰因身材火辣和短劇中的亮眼表現,商演和代言邀約不斷;非科班出身的馬秋元憑借《小魔女秋元》等短劇迅速走紅,被網友譽為“短劇趙麗穎”,單日演出費已達4萬元。
短劇市場的崛起正在重塑影視藝人的評估體系。過去,娛樂圈長期依賴資源和人脈,而如今數據和市場結果成為核心指標。例如,2024年春節期間上線的《我在八零年代當后媽》僅拍攝10天,后期制作經費8萬元,但單日充值額度達2000萬元,抖音話題播放量超8.2億,微博閱讀量破億,相關演員從18線藝人躍升為網紅。
短劇的價值逐漸被更多文化創作者認可。華東師范大學文學系教授湯擁華通過一篇名為《一個中文系教授沉迷短劇的365天》的文章走紅網絡,他觀察到短劇中常設置的“偷聽心聲”特異功能,反映了當代人渴望理解彼此的情感需求。在學術建制化的今天,短劇成為一種對抗窠臼的方式。導演賈樟柯也在微博上分享了對短劇的看法,他認為卓別林的《淘金記》可視為短劇鼻祖,并在2025年平遙國際影展上特別設置短片創投單元。制片人張苗在長春電影節上指出,電影人應向短劇學習,用更簡潔的方式建立人物,吸引觀眾回歸影院。
短劇的海外影響力也在擴大。海外華人將成功劇本翻譯成外語,聘請本地團隊拍攝,使歐美觀眾對“霸道總裁愛上我”等題材產生濃厚興趣。報道顯示,海外短劇平臺ReelShort在2023年至2025年下載量驚人,曾登上美國蘋果商店總榜前三。茶百道、歐萊雅、三星等品牌開始推出自有短劇,并在劇情中植入產品,刺激觀眾消費。
用戶觀影習慣的改變是短劇崛起的關鍵因素。隨著日均刷短視頻時間突破2小時,傳統一小時劇集已難以適應碎片化場景。一些電影人意識到,不是短劇搶走了觀眾,而是觀眾的視聽習慣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快節奏時代,適應速度將決定行業的生存空間,影視行業的變革本質上是行業演進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