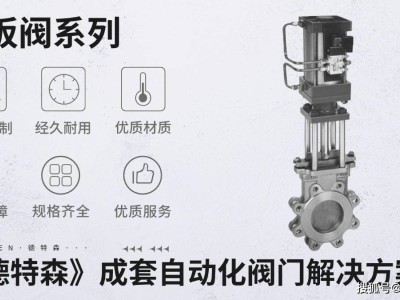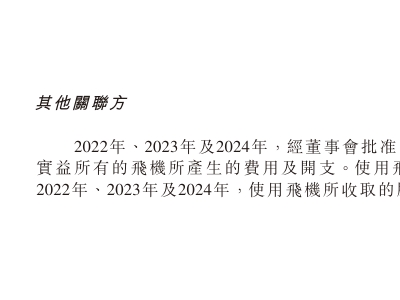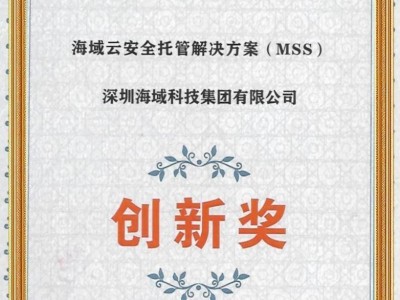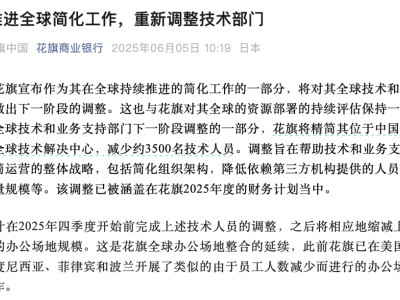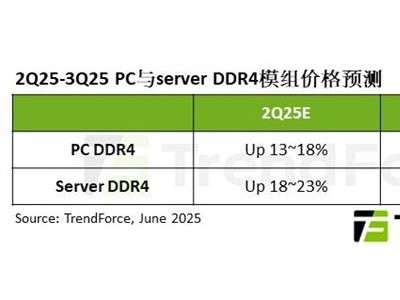在北京東三環外的十里堡地鐵站,王兵,一位62歲的老人,總是最早到達。他身著厚重的衣物,鉆進他那輛紅色的三輪車,開始了一天的工作。這座城市還在沉睡,天際線剛剛泛起微光,而王兵已經準備好,將第一波通勤的年輕人送往城市的各個角落。王兵曾是北京第一機床廠的鋼鐵搬運工,退休后的他選擇繼續工作,每天與年輕人并肩作戰。
王兵與年輕人在三輪車上的互動,不僅是兩代人的日常交集,更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代際變化的縮影。隨著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超過3.1億,適齡勞動人口連續三年大幅減少,銀發再就業議題逐漸浮出水面。然而,這一話題卻常常被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社會焦慮所掩蓋,形成了“非此即彼”的誤解。
事實上,銀發再就業的現狀遠比想象中復雜。前程無憂發布的《2022老齡群體退休再就業調研報告》顯示,68%的老齡群體退休后仍有強烈的就業意愿,其中男性求職者再就業意愿更高。他們重返職場的動機多樣,有的尋求個人和社會價值,有的希望增加收入,還有的則希望繼續發揮一技之長。
韓彬,一位2017年從體制內退休的老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認為自己身體硬朗,無法接受退休后賦閑在家的生活。于是,他不斷學習新知識,涉足不同領域,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不落后于時代”。而山東濟寧市的馬劍,則雇傭了眾多老人來管理他的1200畝桃園。這些老人大多出于經濟壓力,希望通過工作補貼家用。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銀發再就業既是老齡群體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主動選擇,也是應對現實生存壓力的無奈之舉。在江蘇省南通市知名的服裝企業業勤服飾,40%的員工都是退休后繼續留用的。負責人坦言,盡管對年輕勞動力有迫切需求,但年輕人往往不愿進入傳統制造業,更愿意選擇相對“自由”的工作。這一現象在全國范圍內具有代表性,大齡勞動者和低齡老年人已成為傳統產業的主要勞動力。
在養老護理領域,銀發再就業的現象更為突出。數據顯示,養老護理員中40歲以上群體占比高達79.1%,而年輕人則鮮少涉足。這些老年人不僅填補了年輕人放棄的崗位空缺,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結構性失業的問題。同時,我國還有大量的離退休科技人員,他們被返聘或聘為顧問,與青年群體形成經驗傳承與技術創新的互補關系。
然而,盡管銀發再就業有著諸多積極作用,但老年就業市場仍處于起步階段。中國老齡協會老年人才信息中心推出的中國老年人才網,求職招聘欄目信息有限,顯示出構建專業服務平臺的迫切需求。相比之下,日本的銀發經濟體系更為成熟。自1980年設立“銀發人才中心”以來,該體系已轉型為企業化運營,為老年人提供了豐富的就業機會。
日本的銀發人才中心通過構建新型社會參與機制,使老年人能夠自主選擇工作時間和內容,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這一模式值得我國借鑒。然而,我國在老年人再就業期間的權益保障方面仍存在諸多不足。與適齡職工相比,退休再就業老人只能與單位簽訂勞務協議,面臨法律地位模糊、社會保障缺失等現實困境。
在老齡化與就業結構轉型的雙重挑戰下,銀發族再就業已成為重塑勞動力市場的關鍵支點。它既不是“搶飯碗”的零和博弈,也不是被動填補空缺,而是代際資源再配置的必然路徑。通過制度創新打破年齡壁壘,通過價值重構消弭偏見,銀發族的經驗智慧與年輕人的創新活力終將形成互補。
在業勤服飾,那些退休再就業的員工像是帶著企業在努力追趕夕陽。他們的堅守不僅延續了產業命脈,更為傳統注入了韌性。而在新興領域,年輕人的創新活力正在開拓新的邊界。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變革。
銀發再就業不僅是時代命題下的代際共生,更是老齡化社會下的一種新生產力覺醒。它提醒我們,真正的老齡化不是終點,而是另一種可能性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