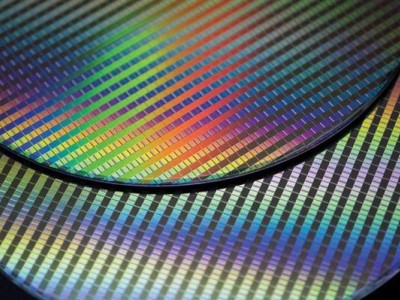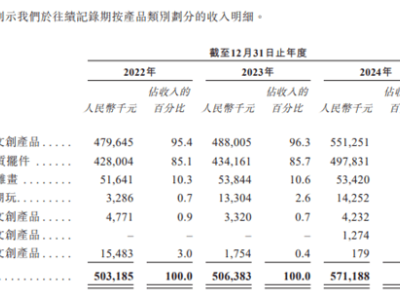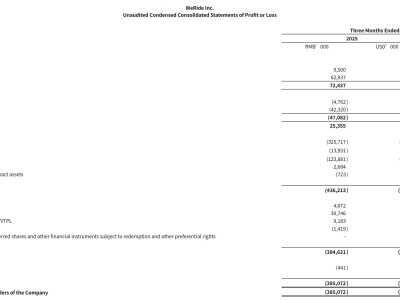在“副業熱”與“AI創業潮”的交織下,一股溫暖而獨特的創業風潮悄然興起:為老年人撰寫回憶錄。這一看似簡單卻蘊含深情的業務,正吸引著一批年輕人的目光。
有人將其視為銀發經濟的下一個藍海,也有人視其為低門檻的副業良機——只需幾千元,聆聽幾小時的故事,借助AI技術,一本“人生傳記”便能迅速出爐。然而,當這些年輕人真正坐在老人面前,聆聽他們緩緩道出那些塵封已久的往事時,他們很快發現,寫回憶錄遠非一門快速致富的生意,而是一場深刻的心靈陪伴之旅。
他與前同事一起,開始了這項充滿挑戰的工作。他們沒有注冊公司,沒有開發平臺,而是從身邊的朋友、社群中開始接單。他們的流程簡單而真摯:口述溝通、文字整理、校對潤色,再到成品裝幀。雖然有時會借助AI工具處理格式和風格統一,但內容始終由人工主導。
然而,張野很快發現,寫回憶錄遠比寫一個品牌故事要難得多。老人們記憶中的細節往往模糊,表達也含混不清,需要反復追問、佐證,才能把那些“說不清”的故事補全。有一次,一位老人回憶自己年輕時從上海去云南參加勞動建設的經歷,由于年代久遠,許多細節都已淡忘。為了還原場景,張野和他的團隊查閱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報紙,甚至找到了同一年代的紀錄片。
在這個過程中,張野意識到,寫回憶錄不僅僅是一項文字工作,更是一次深度的陪伴。老人們其實很愿意講,只是沒人聽。他們通過電話溝通、文字整理,把那些慢慢被忘掉的生活場景一點點拼回來。這種陪伴,讓老人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一生。
起初,張野對AI抱有極大的希望,認為它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然而,實際操作后,他們發現AI無法替代人的情感和理解。AI可以整理邏輯、統一語法,卻無法理解一個沉默背后的悲傷,也無法分辨“他說累了”和“他不想再說”之間的區別。有一次,一位老人在談到年輕時下鄉插隊的經歷時,中途停頓了很久。AI卻繼續輸出了一段“陽光灑落田野”的環境描寫,這種錯位讓場面顯得失真且殘忍。
張野逐漸明白,回憶錄從來都不只是“記錄”而已。它是一個人對自己過往的梳理,是一次“口述—傾訴—沉淀”的過程。有一次,一位78歲的老人在溝通了八次之后,才第一次談起自己早年失去兒子的事。在此之前,他每次都略過那個年份,只字不提。直到那一天,他主動提起,說:“現在好像可以講一講了。”這種心靈的釋放和傾訴,是AI無法替代的。
張野記得第三位客戶,一位74歲的退休中學語文教師。第一次上門溝通時,老人話不多,只遞來一疊泛黃的筆記本和幾張老照片。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里,他斷斷續續和老人見了七八次。通過不斷的交流和反饋,他們共同搭建出一套可被書寫的結構。老人拿到樣稿時沉默了許久,只說了一句:“這些年我一直以為自己沒什么可說的。現在才知道,我其實一直在想。”
然而,張野也越來越清楚,寫回憶錄不太可能成為一門“人人都能賺錢”的好副業。社交媒體上雖然出現了不少打著“回憶錄寫手”“口述史自由職業”旗號的內容,但現實遠比想象中復雜。回憶錄不是標準化產品,每一位老人背后都是獨一無二的人生路徑。除了時間成本,還有溝通成本和信任門檻。付費意愿的落差也是一大難題。愿意花幾千塊請人寫自己一生的老人仍然是極少數。
張野遇到過不少因寫不下去而被客戶投訴的情況,也有低價攬活卻做不出內容的情況。他感嘆這行退場率特別高,指望寫回憶錄發家致富的人大多會失望。他現在把這項服務當作一項“慢慢培養”的事業,精力有限時就不接新單,接下來的客戶只靠口碑推薦。
價格,始終是最難越過的門檻。對許多老人而言,他們往往低估了自己人生的厚度,也高估了“寫回憶錄”的門檻與代價。他們不相信有人會真誠地傾聽他們的故事,也害怕“付了錢寫完之后也沒人在乎”。與此同時,年輕寫作者也在價格上陷入進退兩難。不少人覺得整理口述稿只是“打字員”的工作,成本不該過高。
然而,張野始終記得那些動人的瞬間。有一位老人看到寫好的初稿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低聲說:“我從來沒想過,我的這些事,原來也能被當作故事寫出來。”這種沉甸甸的分量讓他相信這件事值得繼續做下去。
在行業之外,也有一些積極的變化正在發生。有人開始在社區開設“口述工作坊”,邀請年輕人陪老人聊天、整理文字;也有學校嘗試把“家族敘事”列入中小學語文教學,鼓勵孩子回家與父母、祖輩溝通;甚至有心理咨詢師將“撰寫回憶錄”作為部分老年抑郁康復計劃的一環。
張野認為,回憶錄行業更像是一種“慢經濟”。它需要耐心、信任、共情,需要把一個人從沉默中慢慢引出來,讓他相信自己的人生值得被聽、被記錄、被留下。寫回憶錄的過程,其實比拿到書更重要。它是一段人生的重組,也是一場跨代的對話。
在這個充滿“效率優先”的時代,一本老人回憶錄顯得格外“慢”。它耗時、費力、不可批量,卻藏著人與人之間最質樸的情感交換。當一個人愿意打開他沉默多年的過往,當另一個人愿意坐下來聽、記錄、梳理,這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溫情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