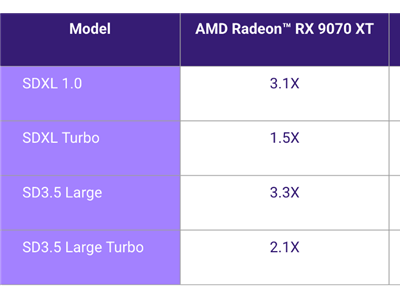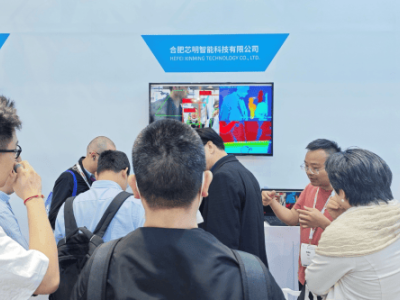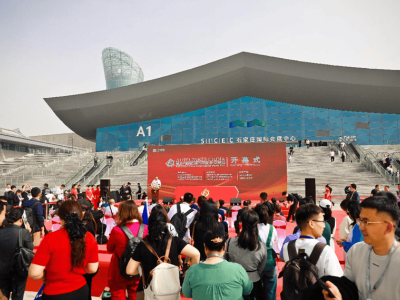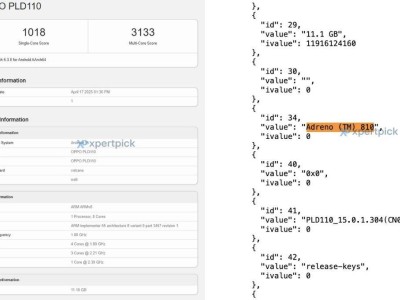5月9日消息 據國外媒體報道,谷歌,百度等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加大對基于神經科學的新型人工智能技術的投入和研發。
有一種理論認為人類智能是源自一個單一的算法。
這個概念始于一組實驗,實驗結果顯示專門處理耳朵所聽聲音的人腦部分也可以處理眼睛所見圖像。雖然只有在人腦處于發育最早期階段的時候才可能有這種情況,但這意味著人腦究其本質,是一臺經過調適可以執行特定任務的通用機器。
大概七年前,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吳恩達(Andrew Ng)偶然發現了這一理論,這改變了他的職業方向,并重新點燃了他對人工智能,即AI的熱愛。吳恩達說,“它讓我平生第一次覺得,我們或許有可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對人工智能夢想的一小部分做出一定的研究進展”
吳恩達說,在人工智能研究的早期階段,當時主流的觀點是:人工智能是源自彼此協作的成千上萬個簡單智能體,也就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馬爾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所謂的“心智社會”。當時工程師們相信要想實現人工智能,就必須要建造并且組合成千上萬個獨立的計算模塊。一個智能體,或者說一種算法模擬語言。另一個智能體處理說話,諸如此類。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他小的時候,吳恩達夢想過建造可以像人一樣思考的機器,但當他上了大學真正接觸到現代人工智能研究的時候,他放棄了。等他當上教授后,他會主動規勸他的學生不要去追求這個癡心妄想。可后來當他偶然聽聞“單一算法”假說,兒時的夢想又回來了。令“單一算法”假說廣為人知的是一位涉足神經科學研究,開發人工智能領域的企業家,杰夫霍金斯(Jeff Hawkins)。
這一轉變改變的遠不止是吳恩達的職業生涯。吳恩達如今在一個被稱為“深度學習”的計算機科學研究新領域領先世界,這一領域旨在建造能以與大腦基本相似的方式處理數據的機器。而這一潮流已經遠遠超出了學術界,蔓延到了像谷歌和蘋果這樣的大牌公司。吳恩達正在與谷歌的其他研究人員合作,建造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系統之一,也就是所謂的“谷歌大腦”。
這一潮流旨在把計算機科學與神經科學相結合,而這在人工智能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吳恩達說,“我發現在工程師和科學家們之間有一道隔閡,隔閡之深出人意料”。他說,工程師們希望能建造能管用的人工智能系統,可科學家們卻還在竭力試圖理解大腦的錯綜復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神經科學界根本就缺乏必要的信息來幫助工程師們改進他們所希望建造的智能機器。
不僅如此,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紅杉理論神經科學研究中心主任,計算神經科學家布魯諾奧爾斯豪森(Bruno Olshausen)說,科學家們經常自以為大腦是他們的專屬領域,所以跟其他領域的研究人員少有溝通協作。
這造成的結果就是工程師們建造的人工智能系統并不一定真正能模擬大腦的運行方式。他們一門心思搗鼓出的那些“偽智能”系統,最后往往更像是Roomba吸塵機器人,而不像動畫片《杰森一家》里的機器女仆羅西。
不過在吳恩達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下,這一狀況已經開始改變。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主任托馬斯因瑟爾博士(Dr. Thomas Insel)說,“現在很多人都有一種預感。那就是誰能夠參透大腦計算奧秘的人,誰就將設計出下一代計算機。”
什么是“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是朝這個新的研究方向邁出的第一步。它的主要內容就是建造神經網絡,而后者模擬人類大腦的行為。這些多層計算機網絡和大腦很像,可以搜集數據并作出反應。它們可以逐漸積累對于物體外形或者聲音的認知理解。
比如說為了模擬出人類的視覺,你可能要建造一層基本的人工神經元,它們可以偵測一些基本的事物,比如一個特定形狀的邊緣。然后下一層神經元可以把這些邊緣組合起來辨別出更大的形狀,然后這些形狀可以被串聯起來以理解某一物體。關鍵在于所有這些工作都是由軟件自行處理的,這大大優于那些老的人工智能模型,后者需要工程師對視覺或者聽覺數據進行修改,機器學習算法才能夠加以消化利用這些數據。
吳恩達表示,有了深度學習,你只要給系統大量的數據,“它可以自行發現某些概念在現實世界中的具體含義”。去年,他的一個算法在網上掃描了數百萬張圖片后,教會了自己識別貓。這個算法并不知道“貓”這個詞,吳恩達要給它提供這個定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學會了全靠它自己,識別出我們稱之為“貓”的毛茸茸的動物。
這一方法的靈感來自于科學家們對于人類學習方式的認識。在嬰兒時期,人會觀察周圍的環境,并逐漸理解我們遇見的物體的結構,但在父母告訴我們那是什么物體以前,我們叫不出它的名字。
是的,吳恩達的深度學習算法目前還沒有人腦那樣準確,也沒有人腦那樣全能。但他相信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吳恩達只是這股大潮中的弄潮兒之一。2011年,他在谷歌公司啟動了深度學習項目。在最近的幾個月里,這個搜索巨頭大大提升了在這方面的開發力度,收購了多倫多大學教授杰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創建的人工智能機構(辛頓教授被廣泛公認為“神經網絡領域的教父”)。中國搜索巨頭百度開辦了它自己的深度學習專業研究實驗室,并承諾會在這一領域投入大量資源。據吳恩達說,像微軟和高通這樣的大型科技公司,都致力于聘請更多在“基于神經科學的算法”方面具備專業知識的計算機科學家。
與此同時,日本的工程師們正在建造控制機器人的人工神經網絡。神經科學家亨利馬克曼與來自歐盟和以色列的科學家們合作,希望能利用數千項真實實驗的數據,在一臺超級計算機中模擬出人腦。
困難在于我們至今仍沒有完全理解大腦的運行原理,但科學家們正在往這個方向努力。中國人正在著手研究他們所謂的“腦網絡組”,并將其描述為一個新的大腦圖譜。而在美國,“大神經科學時代”的大幕正借助于一些雄心勃勃的跨學科項目徐徐拉開,其中就包括奧巴馬總統最近宣布的(也是備受批評的)“使用先進革新型神經技術的人腦研究計劃”(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 Initiative),簡稱BRAIN。
BRAIN的規劃委員會在上周六舉行了他們的首次會議,并預定在本周召開更多會議。它的目標之一是開發可以繪制出大腦復雜回路的新式技術。有跡象表明這個項目也會集中研究人工智能。為這一項目撥付的聯邦科研經費中有五千萬美元來自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超過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提供的經費,而該國防部研究機構希望這一項目會“催生新的信息處理架構或者新的計算方法”。
如果我們能搞清楚成千上萬的神經元是如何彼此相連的,以及“信息是如何在神經網絡中儲存和處理的”,像吳恩達和布魯諾奧爾斯豪森這樣的工程師就可以更好地構思出他們的人造大腦應該是什么樣。這些數據最終可能會豐富并改進深度學習算法,而有很多技術以這一算法為基礎,比如計算機視覺,語言分析以及蘋果和谷歌等公司出品的智能手機上提供的語音識別工具。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算神經科學家布魯諾奧爾斯豪森表示,“我們要從這個方面入手了解生物機能的計算奧秘。我想關鍵在于生物機能把這些奧秘藏得很好,我們只是沒有正確的工具來把握其復雜性”
世界需要什么
隨著便攜式設備的興起,破解神經系統奧秘的重要性前所未有。隨著新設備變得越來越小,我們需要找到新方法來提升它們的運算速度和精度。隨著制造電子設備的基礎元件晶體管尺寸不斷縮小,讓它們更精確更高效的難度也就越來越大。比如說,如果你加快它們的運算速度,那就意味著它需要更多電能,而更多電能會讓系統更“嘈雜”,也就是說更不精確。
奧爾斯豪森認為,如今工程師們的做法是繞過這些問題,他們在速度,尺寸和能耗之間拆東墻補西墻,讓他們的系統實現功能。但人工智能可能會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奧爾斯豪森表示,“我認為不用再逃避這些問題,生物機能或許可以告訴我們如何應對它們… 生物機能使用的開關機制也是天生嘈雜的,但生物機能找到了一個好辦法來適應和忍受這些干擾噪聲并加以利用。如果我們可以弄清生物機能應對嘈雜計算元件的自然方法,就會開創一套截然不同的計算模型”
但科學家們的目標并不只是小型化。他們正試圖制造出擁有一些前所未有能力的計算機。不管算法有多么復雜,如今的計算機都沒法替你去商店購物,或者挑選你可能喜歡的一個包一條裙子。那需要一種更加先進的圖像智能,以及一種儲存和召回相關信息的能力,這非常類似于人類的注意和記憶機能。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將會開啟無限可能。
奧爾斯豪森預計,“所有人都意識到如果你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就會釋放出非常巨大的商業價值潛力”
而正是這一商業前景使得像谷歌,IBM,微軟,蘋果,百度以及其他的一些科技巨頭們,為了開發出最好的機器學習技術,不惜展開一場軍備競賽。該領域專家,紐約大學的延恩勒昆(Yann LeCun)預計在未來的兩年中,我們會看到深度學習新興企業大量涌現,其中很多會被大型機構兼并。
但即使是最好的工程師也不是大腦專家,所以讓更多的神經科學知識易于被掌握很重要。百度公司的余凱表示,“我們需要與神經科學家們更緊密地合作”,他正在考慮聘請一位神經科學家。他說,“我們已經在這么做了,但我們還要在這方面做得更多。”
吳恩達的夢想正在逐漸變為現實。他說,“它給了我這個夢想或許能夠實現的希望,不,不只是希望。我們目前顯然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算法。這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不會是一個簡單的算法,但我想希望就在眼前。”(盧雄飛)
“它讓我平生第一次覺得,我們或許有可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對人工智能夢想的一小部分做出一定的研究進展”— 吳恩達
吳恩達表示,有了“深度學習”,你只要給系統大量的數據,“它可以自行發現某些概念在現實世界中的具體含義”。
生物機能把這些奧秘藏得很好,我們只是沒有正確的工具來把握其復雜性— 布魯諾奧爾斯豪森
如果我們可以弄清生物機能應對嘈雜計算元件的自然方法,就會開創一套截然不同的計算模型 — 布魯諾奧爾斯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