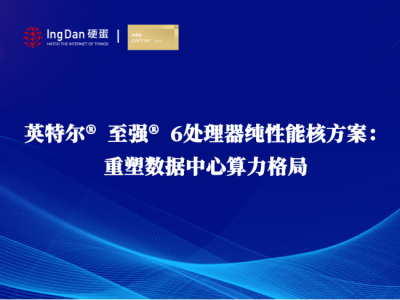西北的秋天,風沙大得出奇。戈壁深處,那座廢棄的邊境哨所孤零零地立在荒原上,像一塊被遺忘的石碑。

段元誠和呂先生沿著干裂的土路走近。路兩旁只有低矮的灌木,風一吹就沙沙作響。哨所的白墻早已斑駁,鐵皮屋頂銹跡斑斑,旗桿傾斜著,頂端什么也沒有。
“以前每天清晨都會升旗。”呂先生停下腳步,抬頭望著那根孤零零的鐵桿,聲音低沉,“一整條戈壁都能看到。”
推門進去,屋里空無一物。灰塵厚得能在地上留下鞋印。角落里殘留一張破鐵床,床腳歪著,旁邊散落著一只掉漆的水壺。墻壁上還能看見褪色的口號:——“寸土不讓。”字跡模糊,但仍能辨認。
段元誠走過去,用手撫了一下那幾個字,手心落下了一層粉末。他沒說什么,只轉身把這一幕收進相機。
二樓是瞭望臺,樓梯窄而陡,踩上去發出嘎吱聲。風透過破碎的玻璃灌進來,帶著冷冽的砂礫。站在高處,遠方是無盡的戈壁,天與地在灰色的線條里融為一體。
呂先生靠在欄桿上,望著遠方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說:“當年站崗的人,從來不看風景,只看有沒有影子動。”他的語氣平靜,卻讓人心口發緊。
段元誠沒有追問。他知道,有些記憶說出來就會破碎,不如讓它留在沉默里。
天色漸暗,風聲在空曠里更顯得尖銳。兩人下樓,院子里荒草叢生,掩沒了當年的腳印。呂先生彎腰,把一塊掉落的鐵片擺正放在墻角,像是在替舊物收拾最后的體面。
“你覺得它會徹底倒掉嗎?”段元誠問。
呂先生搖搖頭,說:“風能磨掉墻,磨不掉它曾經守過的東西。”
太陽完全沉下去時,他們走出哨所。遠處的戈壁線上閃過一瞬車燈,隨即消失在風沙里。回頭望,那座廢哨在暮色里模糊得幾乎看不見,但仍像一只執拗的眼睛,靜靜凝望著無人經過的邊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