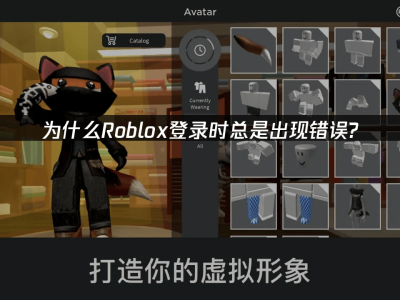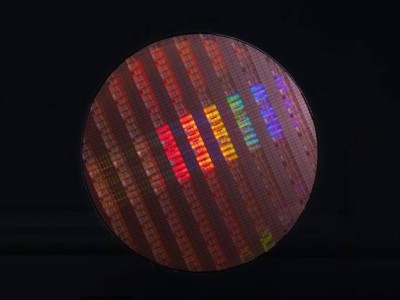在北京朝陽區的一個社區服務中心外,一張褪色的海報靜靜地貼在玻璃門上,上面是關于打車軟件使用的教程。每天,72歲的李建國都會經過這里,心中暗自嘀咕:這些掃碼、注冊、綁卡的步驟,對他來說,比當年考駕照還要復雜。他的遭遇并非孤例,根據老齡辦的調查數據顯示,70歲以上的老年人在使用網約車服務時,叫車成功率僅為40%,遠低于年輕人的90%。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3億多的銀發族似乎被甩在了數字鴻溝的另一邊。
李建國們的日常出行面臨著諸多挑戰:復雜的軟件操作如同解謎游戲,現金支付時常被司機拒絕,而在路邊招手打車時,出租車往往亮著“空車”的標志呼嘯而過。一項針對北京社區的調查顯示,65歲以上的老年人平均需要11分鐘才能完成一次網約車呼叫,其中23%的老年人最終因操作超時而失敗。

這背后折射出一個嚴峻的數字斷層。某打車平臺的內部數據顯示,老年用戶的訂單取消率是年輕人的4.2倍,而這并非因為他們善變,82%的取消訂單是因為老年人“找不到上車點”或“不會修改目的地”。更為嚴重的是,傳統出租車對老年乘客的隱性拒載率高達28%,司機們往往以“送老人去醫院太耗時”或“攙扶摔倒可能要擔責”為由拒絕搭載。
然而,在亦莊試點社區,一種名為銀色叫車樁的新設備正在改變這一現狀。老年人只需用老年卡輕觸感應區,或對著麥克風說出目的地,3分鐘內就會有無人車響應。而在武漢,百度Apollo測試的“招手即停”功能更為便捷,只需監測到老年人的舉手動作,車輛就會自動靠邊并語音確認目的地。
這種無人車的出現,不僅帶來了便利,更體現了技術的安全性。搭載激光雷達的無人車能提前8秒預判老年人蹣跚過街的行為,其制動距離比人類司機縮短了60%。武漢交管的數據顯示,在蘿卜快跑運營半年的時間里,老年乘客的事故率為零,而同期傳統出租車發生的涉老事故多達17起。交管部門的對比測試還發現,面對同一組老年受試者,出租車司機平均在詢問2.3次后就表現出不耐煩,而無人車系統則可以重復應答48次而不降速。
這種無差別的服務正在創造新的可能性。某養老院利用無人車定期接送失智老人進行復查,護理主任發現,車輛每次停靠的位置都分毫不差,后門永遠正對著臺階。如果張亞勤預言的5000萬輛市場規模得以實現,那么每個縣城都將能夠擁有標準化的出行服務。
然而,盡管無人車帶來了諸多便利,但仍有一些挑戰需要克服。當前,單臺無人車的造價高達150萬,足夠購買20輛燃油出租車。將激光雷達的成本降低到5000美元以下,某車企工程師表示他們花了7年的時間。根據《中國老年出行白皮書》顯示,72%的老年人仍然堅持認為“沒有司機盯著路況不踏實”,這種信任的建立需要時間。
法規的滯后也是一個明顯的問題。當無人車為了避讓突然沖出的孩子而撞上護欄時,責任應該由誰承擔?是算法開發商、車輛所有者還是云服務商?目前,在39個自動駕駛試點城市中,僅有12個出臺了具體的事故處理細則。
在上海的一個弄堂里,無人車最近新增了“代買早餐”的功能。張奶奶現在可以用買藥剩下的零錢給孫子買粢飯團。這一細節印證了張亞勤的觀點:“無人駕駛要跨越的不是技術高峰,而是人文海拔。”當AI司機開始理解老年人摸遍口袋找零錢的窘迫時,技術才真正開始彌合數字鴻溝。
科技的意義在于讓每個人,包括李建國這樣的老年人,都能體面地到達目的地。就像那輛在雨中多等待了3分鐘的無人車一樣,它不知道什么是數字鴻溝,只知道要把每一位乘客都平安送回家。